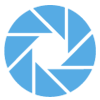品名篇佳作,观世间百态,享人文情怀
图文/朱红琼发自陆良 首席编辑/方 孔
图片编辑/彭外先
【原创作品,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转载】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高中毕业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毕业后进了县烟草公司,工作岗位一直在生产一线,与泥土密不可分。出身农门的我,本想跳出农门,跳进“龙门”,可命中注定与泥土逃脱不了干系,一辈子与泥土结缘。因此,对泥土自始至终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从我记事起,土地就是我最亲热的小伙伴。记忆中,父亲在生产队烧过一段时间的窑。那时,每天放学,我和村里小伙伴就挑着粪箕到生产队的窑上,拾碎炭,空余时间玩泥巴成了我儿时的记忆。

烧窑时,每次父亲搜火后就会产生一些碎炭块,只要生产队管火的会计将大的炭块提出后,说声余下的不要了时,我和小伙伴们就在煤灰里掏拾碎炭块,回家做烧火的燃料补贴家用。

不拾炭的时间,我们总是喜欢到做坯子的泥塘里取做砖瓦剩下的碎泥巴捏成各种各样的玩具,有泥娃娃,泥盆,泥锅、泥碗,泥桥、泥房子等等。那时我的衣服上是除了煤灰,基本上都就是泥巴,就为这个,也没少挨父母的责骂。

应该说,泥土陪伴了我的童年,虽然那时精神和物质都比较匮乏,可成年后的好多思想雏形都来源于那段时光。后来,父亲被生产队改行做了马车驾驶员,在外搞运输。我也就失去了玩泥粑的机会。

但每年的春天,父亲总会回来队里干一段时间的农活,然后再外出搞运输。父亲干活时,只要放学,我就会跟在我父亲的身后,看他用牛犁地,土地在父亲的身后留下一条长长的小沟,我就会用小手抓一把泥土,在鼻孔下闻了又闻,那种来自大地的清香至今记忆犹新。

新翻的泥土里会出现很多的蚯蚓,蚂蚁和冬眠刚醒的小 青蛙。有时,我一个人也会躺在地上,看天上漂游的白云,和空中飞翔的小鸟,听小蜜蜂欢快的歌唱。那时,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就可以飞翔蓝天,飞出陆良坝子,见识外面更大的世界。

1979年后,土地下放到户,父亲也告别了生产队的马车运输行业,回到家中打理自家的责任田。半年后,父亲被村委会推荐到隔壁村庄的社办中学做后勤工作。再半年后,我小学毕业也考到父亲所在的社办中学上初中。三年初中,父亲一直用自行车带着我上学。

周末放学,我与父母一起下地干活。挖地,翻晒,放水泡田,耙田找平,栽秧,薅锄杂草,追肥,每样都不少。最怕做的农活是秧苗移栽还苗后下田薅锄杂草,每一措秧苗的空格处都要薅锄到。每次薅锄结束,脸都会被秧苗摩擦得不成样子,红扑扑的,痒痒的,好多天都恢复不了。

但每当脚踩在水田里,稀泥粑从脚拇指缝冒出的那个爽劲,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心里又爱又怕,爱的是期待着下一次的水田薅锄,再次重温脚在稀泥巴的那个爽劲,怕的是自己的脸又要再次遭殃了。

初中毕业后,我考进了县城的高中,吃喝拉撒睡全部在学校解决。当时住的是苏联式的砖木结构的楼房,宿舍的后面有个小花园。每次下雨,放学后,自己就会脱下鞋光着脚到小花园的泥土地上走一走,真正的靠自己的皮肤接着了地气。班里的同学有点不理解,可我自己知道,我对泥土有着诉说不清的情节。

高中三年,自己不再每周都回家。为了节省车费,从最初的两周回一次家,变成三周回一次,最后变成五周回一次,省下的车费最后都变成了自己喜欢的书。虽然县城走的大都是水泥路,但县城的周围到处都是农田。周末看书累了,就到农田里走一走,寻一片清静之地,坐下来,听一听蛙鸣,闻一闻泥土的气息,解一解学习的疲乏,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高中毕业后,自己考上了省城的农大。入学第一天,办完入学手续后,在农大教书的表哥带着我和父亲到学校的农场里转了转,并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心里准备,农学院的学生许多生产实践课程都会在农场里完成,会有没完没了的农活等着我们去做。

也许是有了表哥的提醒,也许是有从小劳作的基础,大学四年,我与同学们在水田里栽秧,种油菜,在旱地里种麦子,种包谷,栽烤烟,种草坪等等,每样农活干起来都还有模有样,我与学校农场的土地有了写不完的爱恋,曾被评为农学系的劳动模范。

假期回到家里跟父母讲学校里所做的一切。父亲听后并没有直接表扬我,而是语重心长的跟我讲,农村出生的孩子,不管你读书读到何处,你的根基里还是农民,做农民,就不能忘本,该学做的农活不但要会做,还要做得好,才不愧为农民的后代。
或许正是受父母农人农语的谆谆教诲,参加工作以来,每次下乡,看到烟农在地里忙活,总有点蠢蠢欲动想帮忙。每次农忙时节,只要周末不上班,都会回家帮忙干农活。时间久了,也有点想逃避,就跟父母说我掏钱请工帮忙。可父亲却说,农民干农活是尽一种本分和义务,世上哪有出钱请人帮忙尽义务的道理。

听父亲说了后,我也不敢当着父亲的面提请工帮忙的事。又过了几年,父母年岁渐渐大了,每到农忙时节,父亲由原来的亲自劳动变为“坐镇指挥”,我们也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偶尔图省心,也会背着父亲偷偷请工帮忙,尽快完成田里的农活。可能是年龄大了力不从心,父亲有时知道了也装作不知道。
但过后,会亲自到农田里看看请工做的效果究竟如何。我明白,父亲在乡亲们眼中是做农活的老把式,他真正的用意不是怕花钱,而是怕出了钱请人帮忙干农活,最后达不到想要的结果,白白荒废了一季的生产,对土地产生内疚。

后来我成家了,也有了小孩,我的母亲就从家里的责任田里给我取了一包泥土,说这是故乡的土,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一定要把它放在家里,说万一外出水土不服时,回家后可以取点放进水里熬过喝下,大人小孩都管用。我想,其实在医学发达的今天,根本就不存在水土不服,但母亲的用意我明白,她是叫我记住,不管我在哪里,不能忘却自己是个农民的后代。
如今,这一小包泥土整整陪伴我了18年,我一直用个土罐保存着。每当我看到它,我就会想起父母的良苦用心。我始终会记住自己是个农民的后代,记住生我养我的故乡——陆良。(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
作者简介

朱红琼,女,1970年生,云南陆良人,1993年7月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农学系烟草专业,中共党员,农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