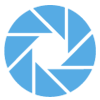编写人:济南中院 曹磊;摘自“鲁法行谈”
▌裁判要旨
醉酒不应一律作为不予认定工伤的事由,而应视职工醉酒与自身伤亡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作区别对待。如果职工醉酒造成行为失控进而引发自身伤亡事故的,对于职工不予认定工伤;反之,如果职工醉酒与自身伤亡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不得以醉酒为由对职工不予认定工伤。
【案号】一审: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行初158号;二审: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终46号。

【案情】
原告:田琼、刘春武、杨新珍、龚夕涵、龚福宥。
被告: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03日22时12分许,杨文成超速驾驶超载的鲁AE9198/鲁AQ032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沿省道102线由东向西行驶,行驶至16公里525.8米处(芙蓉茶楼路口)时,与饮酒后由南向北通过路口的行人龚大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龚大刚死亡,车辆损坏。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文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龚大刚不承担事故责任。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检验鉴定报告》检验意见为:杨文成静脉血中未检出乙醇成分,龚大刚心血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204㎎/100ml。2016年12月23日,第三人济南黄河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路桥公司)向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提交龚大刚工伤认定申请表。因缺少材料,市人社局向黄河路桥公司作出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材料补正后,市人社局于2017年1月10日予以受理。2017年2月6日,市人社局作出F201701001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龚大刚,男,黄河路桥公司职工。2016年12月3日22时12分,该同志与同事在饭店吃完饭后准备返回项目部,步行至省道102线16公里525.8米处时被一半挂车撞到致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检验鉴定报告》载明龚大刚发生交通事故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204㎎/100ml。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醉酒或者吸毒的”不得认定为工伤。《实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中的醉酒标准,按照《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执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医疗机构等有关单位依法出具的检测结论、诊断证明等材料,可以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规定醉酒的标准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100ml,《检验鉴定报告》证明龚大刚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204㎎/100ml,已经达到醉酒标准。据此,本机关对龚大刚同志死亡,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审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记载龚大刚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属于饮酒后的状态,并且《检验鉴定报告》中也明确记载检验意见为龚大刚血液中检验出乙醇成份,含量为204mg/100ml。工伤保险的建立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也是为保障公民在年老、工伤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一)故意犯罪;(二)醉酒或者吸毒;(三)自残或者自杀;(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该条系关于不认定为工伤情形的规定,而该条第(四)项是授权法律、行政法规可以对工伤认定的排除作出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了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具体条件,同时该条例第十四条的部分内容和第十六条也明确出现“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醉酒或者吸毒”等特殊情形时,职工虽然符合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但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因此,《社会保险法》与《工伤保险条例》在本案适用上并不存在矛盾。本案中,龚大刚系工作结束后与同事一起外出用餐时饮酒,其在返回时所受伤害并非发生在工作中。龚大刚在交通事故中其本人虽不承担责任,即使其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但因其属于醉酒,仍不得认定为工伤。综上,市人社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田琼、刘春武、杨新珍、龚夕涵、龚福宥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田琼、刘春武、杨新珍、龚夕涵、龚福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争议焦点问题为:醉酒是否一律成为认定工伤的阻却条件。该法律适用问题之所以产生争议,系因《工伤保险条例》与《社会保险法》对此做出了不完全一致的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一)故意犯罪;(二)醉酒或者吸毒;(三)自残或者自杀;(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可以看出,《工伤保险条例》与《社会保险法》关于醉酒不予认定工伤的规定是不一致的。从文义上理解,前者规定无论醉酒与职工伤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均不得认定为工伤;而后者规定中“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表述则强调了醉酒与职工伤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即醉酒造成行为失控进而引发职工伤亡事故的,对于职工伤亡不认定为工伤;反之,如果醉酒与职工伤亡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不得以醉酒为由不予认定工伤。此为两规定文义解释效果不一致之处,也是本案争议产生的根源,需要解决法律规范竞合的选择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按照此规定,《社会保险法》在效力上高于《工伤保险条例》,两规定出现不一致时,应当以前者规定为裁判依据。因此,就醉酒是否作为认定工伤的阻却条件而言,应当以《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为评判标准,即如果醉酒行为系职工伤亡事故的引发原因,则醉酒成为认定工伤的阻却条件;反之,则醉酒不应成为认定工伤的阻却条件。回到本案,龚大刚在交通事故发生时虽处于醉酒状态,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龚大刚不负事故责任,这说明事故的发生并非龚大刚醉酒所致,即龚大刚醉酒与交通事故发生、龚大刚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及一审法院在未区分醉酒与伤亡事故发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单纯以醉酒为由不予认定龚大刚工伤,属法律适用不当,应予纠正。五上诉人要求撤销市人社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另外,行政诉讼司法审查范围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市人社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对于龚大刚不予认定工伤的事由为“醉酒”,该决定书对于龚大刚死亡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并未进行认定,因此,本院对五上诉人关于此事实的上诉理由不予审查。同时,工伤认定需要综合考虑工作原因、工作场所、工作时间等要素,本院认为醉酒不应成为龚大刚认定工伤的阻却事由,不等同于认定龚大刚构成工伤。至于龚大刚是否构成工伤属于市人社局行政职权范围,应由其依法重新作出认定。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行初158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F201701001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三、被上诉人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重新作出关于龚大刚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
▌评析
本案系因法律规范竞合导致的法律适用疑难案件,如果法官能够谙熟法律规范竞合的选择适用规则,案中难题自可迎刃而解,并可避免无的放矢、自相矛盾的说理论证。同时,本案涉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范围、目的解释的功能与适用条件等较为复杂的法理问题,值得我们结合案件进行深入的分析讨论。重点来说,透彻理解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尤为重要。
一、掌握法律规范竞合的选择适用规则
法律规范由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两部分构成。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发生重合或者交叉,而使同一法律事实为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所涵摄,这种情况被称之为法律规范竞合。[①]在法律规范出现竞合的情形下,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不同的法律效果:一是法律效果完全相同;二是法律效果不同,但可以同时并存;三是法律效果不同,且不可并存。对于第一种情况,不会引起法律适用争议,无需过多探讨。对于第二种情形,通常被称之为“并存式法律竞合”,[②]此时多需要借助体系解释等方法对不同的法律效果进行统一,整合出一个无矛盾的结论。对于第三种情形,因为法律效果不同,且不能兼容,构成规范之间的冲突,通常被称之为“冲突式法律竞合”。本案中,《社会保险法》与《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醉酒不予认定工伤”的规定不尽相同,前者虽然规定醉酒系工伤认定阻却事由,但同时要求职工伤亡系醉酒所致,即醉酒与职工伤亡之间应当具有因果关系,后者仅规定醉酒系工伤认定阻却事由,对因果关系未作限制。两法均对“醉酒不予认定工伤”作出了规定,但是,两法对本案事实进行涵摄后却产生了不同的法律效果,并且两种效果无法兼容或互为补充,形成“冲突式法律竞合”。
面对“冲突式法律竞合”,法官需要运用法律规范竞合选择理论对矛盾予以化解。法律规范竞合选择理论主要包含“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三个选择规则。“冲突式法律竞合”既可能发生在同位法之间,亦可能发生在异位法之间。当法律竞合发生于同位法时,应适用“新法优于旧法”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规则;当竞合发生于异位法时,应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本案中,《社会保险法》与《工伤保险条例》分属不同的位阶,前者系法律,属于上位法,后者系行政法规,属于下位法。两者的冲突应当通过“上位法优于下位法”选择规则予以解决,即本案应当适用上位法《社会保险法》而非下位法《工伤保险条例》进行裁判。因此,醉酒是否成为工伤认定阻却事由应当考虑醉酒与伤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职工在工作中因醉酒导致行为失控进而对自己造成伤害,不认定为工伤,而职工在工作中醉酒但因其他原因导致对自己造成伤害,应认定为工伤。[③]本案中,市社保局及一审法院均未认识到两法之间的不一致,反而认为两法之间并无任何不同,造成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不当。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现行《工伤保险条例》于2011年1月1日生效,而现行《社会保险法》于2011年7月1日生效,从生效时间看,《社会保险法》系新法,《工伤保险条例》系旧法。但是,本案并不能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竞合选择规则,因为该两法并非同一位阶。
二、保持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行使边界
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权力,即通过司法权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进而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行政权的本质是管理权。就权力行使的先后顺序而言,应当是先有行政执法权,后有司法审查权。但是,两种权力均来源并负责于最高权力机关,并无大小之分,而应当根据分工各自限制于自己的领域,保持权力行使的边界。因此,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即司法权不能替代行政权。[④]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认可在诉讼中法院应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尤其是在一些技术性强的领域。因为司法机关既无强制,又无意志,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须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⑤]就工伤认定而言,对于死者是否构成工伤,涉及死者是否系合法供职的劳动者、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要素,对于上述事实的查明属于技术性领域,需要通过行政执法权进行调查完成,而不能通过司法权予以解决。如果司法权以“根本解决行政争议”为由强行对上述事实予以调查认定,则逾越了司法权的边界,僭越了行政权。本案中,市人社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醉酒为由”对死者龚大刚不予认定工伤,从该决定书认定事实内容看,市人社局并未对龚大刚伤亡发生是否在工作时间进行调查和认定。因此,法院应仅就市人社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的正确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而不应超越审查范围。
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关于“龚大刚系工作结束后与同事一起外出用餐时饮酒,其在返回时所受伤害并非发生在工作中”的认定,超越了司法权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系司法权的不当行使。二审法院认为“对龚大刚死亡是否发生在工作中的事实不予审查”,并明确工伤认定的权力系行政权职责范围,系对一审法院不当审查的纠正。综合以上分析,工伤的认定系行政权行使范围,工伤认定是否合法系司法权判断范围,无论行政机关对工伤认定正确与否,法院均只能作出合法性评价,而不得替代行政机关径行作出工伤认定。两权力的区分正如足球场上的球员和裁判,球员只负责踢球,裁判只负责吹哨,即使裁判拥有一流的球技,亦不得在比赛中触碰足球。因此,在工伤认定书没有对龚大刚死亡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即使出于诉讼效率和根本解决行政争议的考虑,法院亦不能对此直接进行认定。
三、避免目的解释的误读滥用
目的解释,是指通过探求制定法律文本的目的以及特定法律条文等的立法目的,来阐释法律含义。[⑥]目的解释的功能在于,当法律文本存在多种解释结论时,通过对于立法目的和旨意的探求,选取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结果。结合本案而言,假如现行法律法规仅有《工伤保险条例》,而没有《社会保险法》。在此情形下,若由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中关于醉酒不认定工伤的规定不够明确(是否考虑因果关系),导致不同法官对该规定产生不同的解释,因上位法缺失,无法通过选择适用上位法以解决争议,则有必要运用目的解释,通过对工伤保险立法目的探究作出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结论选择。整体而言,目的解释有助于实现立法意图,在法律解释中具有重要的价值。[⑦]正是如此,目的解释给予解释者以最大的自由空间,让解释者“自己的理性”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目的解释给裁判者带来宽松的解释自由,导致人们对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和信赖,并错误地认为目的解释是一把通用的“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任何疑难案件中的困惑之锁。本案一审即是对目的解释滥用的典型。本案所面临的疑难问题属于两个法条竞合时对法律规范的选择适用问题,而非同一法条出现多个解释结论时对解释结论的选择问题,因此,应当通过“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对本案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予以解决,而无须更不应运用目的解释对工伤保险的立法目的和精神进行探究。一审判决颇费笔墨地阐释工伤保险的立法目的——保障伤亡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然而,一审做出的判决结论却与其探究的立法目的相背而行,让人对其运用目的解释的意图深感不解。一审所犯错误在于,未对目的解释功能及适用条件进行考察,在不应当适用目的解释的情况下错误对其适用。简言之,本案根本不具备适用目的解释的条件,即便是在二审判决中,关于工伤保险立法目的的探究亦非锦上添花之举,而是多余的。
[①]孔祥俊:《法律方法论》(第一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②]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③]杨雄科:《工伤认定标准与法律适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163页。
[④]参见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法学》1998年第8期。
[⑤]彭涛:《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处理规则》,《法律科学》2016年第6期。
[⑥]王利明:《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页。
[⑦]张志铭:《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