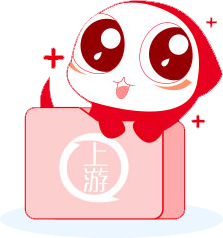

上游观剧|法国话剧导演萨维提耶:《雪》是对戏剧源头的一种回归
上游观剧NO.33
法国话剧《雪》
法国斯特拉斯堡国家剧院作品
重庆大剧院2018年7月19日演出
女导演布朗蒂娜·萨维提耶个子高挑,走路带风,眼里闪现着法国女性的聪明,或者说是某种狡黠。这种特质在不少知识女性身上似乎普遍存在,转化为舞台智慧往往能收获不错的效果,萨维提耶献出的话剧《雪》便是这样一部杰作。

剧照。
《雪》的来头很大,原作者是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当然他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作品是《我的名字叫红》。操刀文学巨匠作品本就压力重重,小说珠玉在前,话剧是另一种艺术呈现,先别说超越经典了,能够在还原的基础上打动观众就很了不起。
更遑论,《雪》的原著厚达700页,书中错综复杂的政治、宗教、文化、历史等背景知识交织成一张巨大罗网,主要人物们在这张网中按照帕慕克的安排上演着喜怒哀乐。如果你读过帕慕克的书,你该知道这位作家的文字仿佛土耳其细密画一样繁复,事无巨细,絮絮叨叨,一个一个阅读陷阱很容易绕晕读者,那么,舞台到底又该如何呈现?
萨维提耶很有胆量,最终把700页小说浓缩在了3.5个小时的话剧中。《雪》问世以后在西方一些国家大获成功,作为2018年“中法文化之春”重点推荐剧目,首次来到中国巡演,陆续亮相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尤其对于重庆而言,原汁原味的法国话剧,似乎还是第一次上演。

男主角与导演。
演出3.5小时,中场休息20分钟,全程法文对白,设计简约充满隐喻的舞台,纪录片一样播放的投影片段、偶尔从观众席间冒出来走上舞台的演员……我相信剧场里的观众一定感受到了挑战,来自体力和脑力两方面,这样的大戏在重庆演出不多,更不要说全程必须借助字幕才能理解情节。
但现场效果却超乎想象。除了零星几个带小孩的年轻妈妈提前退场,几乎所有观众都坐到了最后。基本上大家都不懂法文,却在中场休息和散场离席后热烈的讨论着话剧心得。热烈的情景是很多国产话剧都不曾有过的。
开演前我曾有的担心真是多余了,或许成功的秘密正如演出前萨维提耶告诉我的那样——
“《雪》是对戏剧源头的一种回归,它关注的人性、情感具有普适性,它已经感动了许多国家的观众,我也有信心打动重庆。”

导演萨维提耶。
对话萨维提耶》》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为何会想到改编帕慕克的《雪》?
萨维提耶:虽然小说1999年问世,但话题具有全球性和强烈戏剧性,适合永久性演出。这种具有人性光辉的主题适合所有语境,展现的戏剧主要冲突来自传统文化和现实世界,反映了不同年代的人们的认知矛盾,人物身份迥异、关系复杂,加上发生在土耳其这样特定的国家,作者也是帕慕克这样世界级作家,他站在一个特殊身份上放眼世界反思身份,既有开放性也有预见性,这部优秀的作品值得戏剧去二次表现。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以法国人身份去诠释土耳其文学,你如何达成跨文化理解?
萨维提耶:伊斯坦布尔连接了欧亚大陆,本身也是一座极具跨文化精神的城市。帕慕克是土耳其人,但对我来说他首先是欧洲公民,他在法国留学多年,浸淫法国文化,我虽是法国人,但我在文化上也是欧洲公民,这一点我和他一样,这种跨文化理解不难实现,其实全世界文化都在交流中融汇,比如中国很多作家在法国也有译本,像莫言很受欢迎的,文学和艺术的东西没有国界,相同的东西是人性。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具体到改编,700页原著如何浓缩在三个半小时中?
萨维提耶:可能中国观众觉得3.5小时有些长了,但这个时长在欧洲只是一个戏剧正常的表达时间,在阿维尼翁戏剧节很多比这时间更长,戏剧的改编其实是二度创作,我希望抓住小说主题去回归戏剧本源,保留了原著中的忧伤,或者叫做“呼愁”的魅力,以及帕慕克安排的非常重要的戏剧冲突,首先是诗人卡的介入,同时以一个戏中戏结构去展示冲突中的冲突,高度凝练,是非常经典的一种戏剧表达方式。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呼愁正是帕慕克作品永恒主题,说说你的理解吧?
萨维提耶:呼愁主题类似于我很喜欢的世界级作家契诃夫经常营造的一种氛围,甚至可以联想到葡萄牙里斯本的传统音乐法多(fado),一种忧伤的诗意之美,帕慕克对呼愁的表现跟他成长的伊斯坦布尔有关,他见证了伊斯坦布尔发展,这座古老城市跟中国一些地方相似,城市化进程、人口增多、面积增大,传统在不断接受现代冲击,城乡二元化带给人的信仰的冲击等,都是戏剧需要的矛盾冲突。
其实戏剧里男主角卡的呼愁正表现了一个人随着成长逐渐消失的天真和快乐,这是成长的代价,小说和话剧就想去定义什么是快乐,这种可能性在哪里,怎样去重新找回快乐?这种哲学层面的思考,也是我想跟观众探讨的。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赵欣 高科 实习生 王偲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