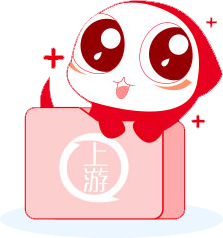

探访强制隔离戒毒所:生理脱毒期是“艰难时间”

6月13日,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操场上,戒毒人员正在整队准备做操。
新京报消息,凌晨4点5分,有人来敲值班室的门。
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下称女所)的干警马丽醒了,但还有点儿恍惚。已经在戒毒所工作了17年的她知道,又“来活儿了”。
对吸毒人员的收治工作就从此刻开始。这次要收治的人,40岁出头,因为吸食传统毒品海洛因,在收治安检的过程中,她不断地打哈欠、流眼泪,“站着不舒服、蹲着不舒服,她自己也不知道要摆个什么姿势才舒服”。但相比有些人毒瘾发作时的胡言乱语和躁狂,她的表现算是正常多了。
因为毗邻毒品产地“金三角”,禁毒形势严峻,云南收治的戒毒人员是其他一些省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目前有约3.4万人在云南省内15个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
近日,新京报记者探访了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和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一部分吸毒人员被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移送到戒毒所。高墙之内,这些人是吸食毒品的违法者,也是毒品受害者和病人。被收治的2年间,他们努力挣脱毒瘾、重建心理,期待回归社会。

6月13日,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未成年人大队,几名喜欢音乐的未成年戒毒人员正在弹琴唱歌。
艰难的生理脱毒期
郑西今年37岁。你问她,这是第几次来戒毒所了?
她那双大眼睛骨碌一下:“10多次、20次了,次数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
郑西从1995年开始吸毒,当时14岁,上六年级。和朋友们在一起,她说感冒了头疼,朋友拿海洛因给她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吸食海洛因,郑西也吃麻黄素、冰毒,这些新型毒品对中枢神经的损伤极大。今年5月9日刚到女所时,她连走路都要两个人搀扶。
警官马丽形容她当时的状态:“流口水、反应很迟钝,你跟她说一句话,感觉声波像隔着十万八千里传到她耳朵里,就像《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一样。”
在云南省唯一专门收治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戒毒所,现在有戒毒人员1400多人,马丽最多一晚就收治过10个,“(收治时)不去刺激她们,她想蹲着就蹲着,觉得躺在地上舒服些那就躺着,等之后清醒一点了再来规范言行。其实等清醒之后,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
按照云南省的戒毒模式,吸毒人员被移送到戒毒所后,要经历的第一步是生理脱毒,生理上对毒品的依赖消除后,经过考核转入康复治疗阶段,期间他们要进行劳动康复、体能训练和心理矫治,最后转入回归适应期。整个流程下来需要2年,表现好的戒毒人员可以减期,但戒毒时间最短不少于20个月。
生理脱毒期,是吸毒人员的“艰难时间”。
24岁的徐婉有2年多的吸毒史,去年9月从工作的娱乐场所被收治进所。经过近9个月的生理脱毒和康复训练,她的体重从刚进来时的52公斤长到了60公斤。
头脑恢复清醒的徐婉说,想象不到自己刚进来时多恐怖,在生理脱毒期时发瘾,用头撞墙,撞出两个洞,忽冷忽热、出汗、头晕、站不稳、吐,过一会儿冷热又开始交替,“当时如果有人跟我说,你把那个人掐死我就放你出去,我会的,一点都不夸张。”
生理上的不可控是戒毒人员要经历的正常戒断反应。一名收治安检时情况还算正常的40多岁戒毒人员,马丽前几天去看她,“腹泻了好几次,裤子都换了8条。”

6月13日,云南省女子强制戒毒所,新进来的戒毒人员正在跳操。
违法者也是受害者
除了是有20多年吸毒史的“瘾君子”,郑西的另一个身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996年,她在一次检查化验中被查出携带HIV病毒,是共用注射器感染上的,有一次毒瘾发起来,来不及去买,用了别人的注射器。
在女所,和郑西一样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30多人。考虑到身体条件的特殊性,女所的艾滋病戒毒人员每天要测3次生命体征,每天早晨9点和晚上9点分别服用抗病毒药物。
2014年,云南开始对患艾滋病的吸毒人员进行集中化专门管理。目前,云南省戒毒局在包括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下称五所)在内的15个戒毒所设立了8个艾滋病专管大队。
五所距离女所大概1公里,收治规模5000人,抵得上某些省份全省的收治量。五所的HIV专管大队,目前共有170人左右。
HIV专管大队的警察、三级警长王勇告诉记者,为了消除隔阂,HIV戒毒人员在日常作息和服装上与其他戒毒人员没有区别,“方便区分管理,只是衣服上的胸牌会标明是几大队。”
王勇1999年参加工作,从2014年五所设立艾滋病专管大队开始,他就管理着这里的特殊戒毒人员。“对艾滋病人集中管理后松了一口气,之前和普通戒毒人员放在一起,总担心会不会交叉感染,成立了专管大队会轻松一些。”
“轻松了一些”的王勇也经历过工作中的“危险时刻”。有一次进行完普通戒毒人员安全检查后,晚上下班时发现手上多了一个伤口,“就使劲想,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在哪儿伤到的,这个时候很惶恐,挨个去翻监控录像,看完发现不是在检查环节上出的问题,这才放了心。”
3年多以来,五所的HIV大队共接收戒毒人员800多人次。王勇说,很多人是老面孔,基本上是家人不管、朋友不理,反反复复进来。
不仅是艾滋病,在全国近24万名戒毒人员中,患各类疾病的人占30%左右。云南的比例更高,在所的3.4万人中病残比例达60%,常见病还有肺结核、肝病、胃肠道疾病、心血管类疾病和精神类疾病等,有的戒毒人员多种疾病加身。
和戒毒人员患病率高的现状相比,目前全系统内医务人员只有281人,他们负责在所内巡诊,一旦戒毒人员在所内无法医治,还要在转移社会医院就医的过程中随诊。戒毒警察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他们一方面要从事戒治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格外注意戒毒人员的身体状况。
因为戒毒人员这些重叠的“身份”,云南省戒毒局副局长宋云奎把他们称为“违法者、受害者和病人”。
在戒毒所重回课堂
六月上旬正值南方雨季,昆明连续下了几周的雨,没有要放晴的意思。天好的时候,女所里康复期的戒毒人员可以到院子里活动活动,做操、唱歌,这有利于她们的恢复。
昆明的夏天到底是好看,戒毒所的路两旁到处开着小花,各种颜色的。女所离长水机场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总有飞机飞过天空。
下雨了,出不去门。上午10点半,警官李云就在教室里给戒毒人员们上课,这节课讲身体恢复方面的理论。讲到体重和饮食,李云问坐在下面的19个人: “你们现在喝酒吗?”
“不喝。”
“在外面喝吗?”
“喝。”
“喝的多吗?”
“多。”
异口同声地答完,又异口同声哈哈大笑起来。
和其他戒毒人员不同,这19个女孩是未成年吸毒者,进所时16岁到18岁不等,这是《禁毒法》规定的可以适用强制隔离戒毒的年龄。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云南在全省设立了2个未成年戒毒人员大(中)队,女性未成年戒毒中队设在女所,目前共19人;男性未成年戒毒大队设在临近的云南一所,现有221人。
云南女所教育矫治科科长宋运香说,和其他戒毒人员相比,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时间更长。警察会结合自己的专长给她们上课,宋运香的课在每周四上午,她最近讲的是汉字演变,中间穿插讲授传统文化。
吴曦喜欢上这些课,说不上为什么,只是感觉上课时心情会放松一些。她没想过自己还能重回课堂。
去年12月12日被送到女所时,吴曦16岁,已经吸毒3年。2014年上初二,学校分班,她跟班上最调皮的一个女生分到同桌,两人一开始不讲话,但同龄的小女生慢慢总能玩到一起。女生带她去见朋友,“那两个人正在吸毒,喊她吸,她有点犹豫,但是吸了;他们又问我吸不吸,我当时特别特别犹豫,但又感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吸没事,那我就陪她一起吸。反正就是她做什么我也陪她一起做。”回忆起最初接触毒品的场景,吴曦低着头,说话声音又小又轻,怎么也脱不了那一脸稚气。
不少未成年人走上吸毒的道路。受人引诱沾染毒品,继而开始逃学、辍学、与家庭决裂。吴曦也是。为了买海洛因,她想尽办法跟亲戚借钱,把爸爸的酒和烟拿出去卖。
有次在家“吃东西”,被中途回家的爸爸撞见,吴曦被锁在家里。后来爸妈带她到别人家做客,上车时她独自跑掉,靠在批发市场或十元店批发了东西转卖给麻将室的阿姨挣钱,和朋友在外面租房子住,这样吸起来更方便。
那年,吴曦14岁。
戒毒?无数次想过。“清醒的时候站在镜子前,摸着自己的脸哭,哭到崩溃,问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一定要戒,不能再吃了,但毒瘾发起来就不想了,瘾一发就没有人性、没有感情了。”吴曦说,自从吸上毒后,自己就变成了这样的“双面人”。
2015年到2017年,吴曦的爸妈带她去成都的医院戒过毒,又给她找过两所职中上学。在戒毒医院,她被各种针水和药物搞到没有记忆、大小便失禁,14天后放弃。在学校,晚上睡不着,每天熬到凌晨四五点,太难受了,又忍不住逃学、辍学,找朋友复吸。
去年12月,本应在昆明读书的吴曦跑回老家楚雄。在网吧,因为身份证显示是未成年人,她被送到派出所。警察许是看出了她的异常,给她验了尿,“第二天早晨我妈一来就跟我说,你要被送去戒毒了,2年。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向警察申请把我送到这里。”
刚进戒毒所时,身高1米6左右的吴曦34公斤,整整一星期又吐又拉,当时她最羡慕已经脱掉毒瘾的人,“如果有力气该多好,自己走路、自己做事”。
强制隔离戒毒半年,吴曦的体重增到了48公斤。家人会见时她告诉爸妈,自己学会洗衣服、整理内务了。
隔着玻璃墙,妈妈对她说:“要保持这些习惯,等出来后也要继续这样。”
反复进出的复吸者
吴曦想过出去后的事,从进戒毒所之后的第二个月就一直在想。
但她还是怕,想出去,又怕出去,因为不相信自己,怕回到原来的环境,又复吸。
对于走进戒毒所和要走出戒毒所的人来说,复吸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在业内,经过强制隔离戒毒之后不再复吸被称为“保持操守”,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增强,目前还没有全国层面的操守保持率和复吸率的权威统计数据。
提到“复吸率”,云南省戒毒局副局长宋云奎也常感到为难,“我们做过几次调查,找到之前戒毒人员进行回访,见面率达到50%,很多人见不到面,而能见到的这些操守保持得也是比较好的,复吸率没有那么高。”
根据去年国家禁毒委发布的《2016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截至2016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50.5万名,2016年全国查获的复吸人员达60万人次。
李乐原本在昆明一个小有名气的乐队做鼓手,大概10年前,他被同乐队的贝斯手“拖下水”,染上了大麻。去年12月进入云南五所,已经是李乐第四次被送进戒毒所。
近10年间,李乐复吸过三四次,间隔长的时候两三年,短则三四个月。在一次重大的演出前毒瘾发作,他和贝斯手跑出去找毒品,回来晚了,演出搞砸了,人也被乐队开除了。
出去后和朋友聚会,本来是喝酒吃饭,但总绕不过毒品,于是又吸在一起,“出去后想做什么?现在说都是空话,这个戒了就一切都有可能;戒不了,就什么都别想。”李乐说,这次出去后不打算留在本地了,想脱离之前的环境。
戒断就像“渡河”
到明年9月,王勇在戒毒所工作就满20年了,他跟一些戒毒人员聊过,为什么在戒毒所里2年好好的,出去又复吸了?
他自己总结了答案:“因为回到社会后没有人接纳他们,之前有一个戒毒人员的家人来探访,只有父母跟他说话,兄弟姐妹坐到一边,全程一句话都不说。那些能戒断的,往往是周围环境和家庭的接纳程度比较好的。”
提到这些年反复进出的面孔,王勇说,复吸不单是个人抵抗力差的问题,更是综合环境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些边境地区,毒品可获得渠道多,如果想真正戒断就要付出很多。
宋运香把戒断的过程比作“渡河”,从这岸到对岸,水里有各种危险,天气变幻莫测,如果足够幸运可能会顺利渡过去,但也可能中途被浪打翻,被重新掀回来,但重要的是,要记得目标是渡过这条河,借助各种力量渡过去。
宋运香说,戒毒所没办法帮戒毒人员选择出所后的朋友圈,要做的是让他们回到正常人的状态,告诉他们,正常的生活挺好的,你有能力这样过,“我们会设定情景,模拟怎么拒绝之前的毒友。能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正确的方向。”
在高墙内,康复期的李乐加入了所内的乐队,他是队长。每周有5天时间,他带着另外4名队员在五所二楼的活动室排练。
李乐坐在乐队最左边,打起鼓来沉稳有力。身旁的主唱唱起汪峰的《彼岸》:
妈妈,
不要为我伤心,不要这样难过,
我还在寻找生活,只是有些挫折。
(注:文中戒毒人员均为化名。)
原标题:脱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