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几乎遗忘的矿山岁月
梁光华
一
我从小就生活在红岩煤矿旁边的菜蔬队,长大后又在红岩煤矿子弟校教书,除了念中师那四年,一直都在矿山吃喝拉撒。如今,煤矿关闭,人们大多迁居外地。然而,不管多少年以后,矿山的人和事,都会如刀劈斧砍般深深镌进我的记忆。一旦忆起,总觉得是那般沧桑、凄凉,并永远在我的心底深处搅动一池皱水,形成一幅幅或清晰或模糊的连环画卷,让我辗转难眠,彻夜沉思……
二
老家就在丛林镇红岩村砖房社。砖房社在计划经济年代属于菜蔬队,主要栽种蔬菜,以供应当地的国营企业所需。菜蔬队的乡亲也像工厂的人一样,拿购粮本吃供应粮。因为供应的粮食不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大家也种植些水稻、小麦、苞谷、红苕……多方筹措家里口粮。
那些年成为一名工人是挺有面子的事情,至少比老师要光鲜得多。因为工人有几十块工资,可以吃“皇粮”,领劳保。如果是在井下一线工作,供应的“皇粮”还要多些。而那时许多农民家庭一年全部的收入也可能就几十块钱,家里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需要钞票呢!
菜蔬队归根到底是农民阶级,社会地位没有工人高,但比农业队又强得多。印象中我的供应粮为十八斤,粗粮、细粮各一半,加上地理位置与红岩煤矿相邻,矿上的学校、医院、车站、澡堂、商店、肉店、粮店、影院……都可以享用,各方面的条件要比纯粹的农村好很多,自然抬高了菜蔬队乡亲的地位。生产队的男孩成了四里八乡姑娘羡慕的对象,而村里有姑娘的人家,往往也是要求男方倒插门,而不将姑娘的户口迁出去。砖房社人口最多时有五百多人,比好多村的总人口还要多。
遗憾的是,我虽然也是砖房菜蔬队的一员,但却一直没有高人一等的感觉,相反,低人一等倒是长期存在。
因为菜蔬队里与我年龄相仿的伙伴并不多,志同道合者则更少。我少年时接触的伙伴大多是厂矿子弟,在他们那儿,我这菜蔬队的身份自然要大打折扣。一是经济上没法比,虽然父亲是红岩煤矿的工人,在那年头被人调侃为“半工半农,辈子不穷”,但我们穿的、吃的、用的,其实是远不如厂矿子弟。没有零花钱,背的是旧书包,很少穿新衣服,就连红领巾也是春生舅找张红布缝制的。有时候,我觉得还不如农业队的孩子,他们的房前屋后还种植有几株果树,而我们什么都没有。
但经济上不是最主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莫须有的自卑感越来越强,感受的工农差别越来越明显。比如南桐矿务局有些煤矿与当地农村发生一些纠葛、矛盾的时候,矿务局教育处会下令各校统计就读的农村孩子,以勒令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转学到地方学校的方式,施压于地方,博弈于各种势力。
这个时候,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竟然与我息息相关了。当然我们的班主任从没有歧视我的意思,也绝对没有歧视农村人的意思,但统计工作还得开展。好在生产队与红岩煤矿在建矿之初征地的时候就有约定俗成的口头协议,所以这些事情最后都不了了之。但每次碰上这些事情,班里的同学往往会起哄,自然会加剧我的自卑感。
三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大家虽然被分为工农阶层,但融为一体是早晚的事。
煤矿的子弟一天天长大,恋爱结婚、娶妻嫁人、生子育女,这是人生必然的规律。但矿上房屋十分紧俏,修建的房屋根本满足不了需要。有人就开始在菜蔬队乡亲那里租房,并渐渐成为一种常态。
我家在红岩煤矿工人村幼儿园后面,地理位置好,来租房的年轻人就很多。
最先到我家租房的是王天容叔叔和张贵阿姨。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王叔叔与张阿姨喜结良缘,为营造自己温暖的小家,就到我家租房。我家房子是石墙瓦屋楼板结构,碰上下大雨还可能到处漏雨。但他们还是租下了最外面那间低矮瓦房,至于租金,好像是每个月五元。
这开了砖房菜蔬队出租房屋的先河,矿上一对对新人,一户户人家纷纷选择到农村租房安家,到后来还出现了个别学生与家里闹矛盾后,自己也搬出来租房,与家里“拜拜”,显示叛逆的倔强。
这种风潮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竟然催生了砖房社的房地产事业。大家觉得出租房子是一项可以长期投资的生意,于是纷纷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翻修房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萌芽,至九十年代中期大规模造房,十余年时间,砖房社里几乎每家都建设起一楼一底几个排面的现代楼房,有几家还修上三四层,活脱脱的“暴发户”。其实,房租最贵时也才一间房一月三十元,还得给他们提供公用厨房,或者是提供地盘,由着他们找来材料,自己搭建简易的毡棚屋。
租房简陋,条件不好,但毕竟是新家庭生活的开始,但过日子就不再是花前月下的甜蜜了,生活中磕磕碰碰总少不了。今天这家租客发生了矛盾,房主就充当和事佬,明天那家租客水火不容,房主又成为灭火器。谈心交心,将心比心,化解矛盾,房主充当了今天社区干部的角色,并且干得不亦乐乎。
一旦哪家租客手头紧,日子过不下去了,房主还主动提出可缓交房租,并开放自家的菜园,送些蔬菜以帮助他们解燃眉之急。而哪家小夫妻喜欢打牌,不小心输掉了生活费,哭闹着要离婚,房主一边借钱帮助他们,一边又充当长辈教训他们,浑然忘记了房主与租客的关系。租客一旦搬家离开,往往依依不舍,相互祝福。
租客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消费,比如看电视、弹吉他、跳舞、唱歌、绘画……也乐于参与农家的劳动。春耕时帮助播种,农忙时帮助收割,闲下来时一起抹苞谷一起聊家常,偏东雨时参与粮食抢收,甚至一起砍柴、挑煤,根本就没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像前面提到的王叔叔就经常帮助我们劳动,可惜后来他因煤矿事故而终身瘫痪,让我们心痛至极。
随着农家经济日渐改善,工农之间通婚也不再稀罕,而农转非后大批矿工家属进入工人村,到农村开辟出许多庄稼地,红岩煤矿与砖房菜蔬队逐渐地融为一体了。
房主与租客经过多年交往,大多感情深厚,渐渐成为常来常往的友朋,甚至是亲戚了。直到现在,我在万盛还时不时能看见一些当年的租客,寒暄间还能回忆起当年的青春岁月。

四
该聊聊我那些命运坎坷的同学了。
李刚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又同属砖房生产队,小时候很多自发的游戏和恶作剧,我们都是共同的参与者,长大后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几乎没再来往,偶尔见面也就打个招呼,简单聊侃几句而已。因为乡里乡亲的缘故,对他家的情况知道一些,他家可谓一贫如洗,他又没有别的技能,为了生计,就当了采煤矿工,以养家糊口。多年前的一个晚上,砚石台煤矿发生一起井下塌方事故导致他的死亡。听我父亲讲,矿上赔偿了几万块,他的母亲和孩子也得到了一定的生活补贴,此事也就了结了。许多人都说矿上想得周到,赔偿得很好,他死得算值了,如果是在农村下地时发生不幸,哪有这样的赔偿哦,有人为此羡慕不已。
按照农村的习惯,他家请来了道士法师、唢呐锣鼓,办起热闹的丧事。鉴于他家经济确实不宽裕,几位德高望重的硕老找到生产队里几位当家的商议后,到山上砍伐大松树做了口棺材,风风光光地将李刚送上山。
一天早上,我在海棠晓月建设银行边碰上小学同学陈一骄,在闲谈的时候,他无意提到了另一位小学同学江米娃,也已经去世了,原因是在煤矿的一次井下事故中受了重伤,据说脑花都砸出来了,抢救了几个月,还是没有活得过来。
一说到江同学的时候,我脑海中立即浮现他的音容笑貌,是那么腼腆,就像一个害羞的女生。读小学时,我们常常在红岩子弟校旁边的警报山一带玩耍,摘野红籽,扒野地瓜,有时候也谈人生、谈理想、谈友情、谈成绩……那片土地几乎留驻了我们小时候的全部快乐。
最近一次见面大约是在2013年5月,几个同学在新房子棚改区偶遇,有人提议中午就在路边餐馆小聚。陈一骄特意回家拿了瓶好酒,大家喝上几盏。记得当时江同学谈到孩子在进盛中学读高中,特恳求我在必要时帮帮忙。也谈到家里一些琐事,特别是八十多岁老母的赡养问题,听得出他十分郁闷。是啊,作为男子汉,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为了生计而忙碌奔波,生活的艰辛,世事的无奈,让他那张曾经充满童真的笑脸荡然无存,代之的是苦闷与忧郁。
没想到,那次相聚,竟是永别。
生命是高贵的,但在煤矿工人那里,在忙碌奔波生计的穷人那里,也就那么回事。
前几年我在万盛步行街租房子的时候,有次碰上霍明夫妇。霍明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也是一个砖房社的发小。因为他儿子在进盛中学学习美术,他买上些东西,非说要给我拜年,并在我那里摆了几个小时的龙门阵。
小时候我们常玩一种叫“打豆腐干”的游戏,他十分上瘾,做了很多豆腐干。我常被拉去参观他收藏的豆腐干,藏在牛圈里,有大大小小好几堆。长大后我们之间没有来往,只知道他也是在煤矿井下出了事故的,好在大难不死,逃过一劫,留下残疾,办了退休手续,拿起了退休金,自己则在家推豆腐卖。再后来因为红岩煤矿工人村人口越来越少,就不再做豆腐生意,跑到贵州某地的小煤矿做起了大师傅。
谈到他遭遇的那次井下事故,谈到现在又到煤矿兼职,他觉得老天待他太好,让他还能见着阳光:“我又不像你那么有文化,不干煤矿的事情,我还能做什么呢?”我问他到煤矿害怕不,他说:“有什么大不了,上班时机灵点,没啥子危险的。”
武关均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小学四年级时,他就从老家来到红岩子弟校,与我一个年级,成绩很好,智商也高。记得学校组织四位同学到104中参加全区的小学数学竞赛,有邓友松、刘利、武关均和我。竞赛完后,我们还一起到红岩平硐他家居住的毡棚屋里看连环画,还记得我看的是《偷拳》。
1987年初中毕业,他考中专差了几分,后来选择就读南桐矿务局技工校,之后顺理成章地分配到煤矿工作。遗憾的是,像他智商这么高的人,在矿上也没有避开危险。一次井下事故让他差点丢命,好在及时抢救而脱险,后来重新拾起书本,边工作边学习,考上了重庆煤校,取得中专文凭,工作几经转折,最后在红岩子弟校成为我的同事。
在我的同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有时我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们还会选择矿山,将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生命交付给矿山吗?
五
谈谈那些年的矿山教育吧。虽然红岩子弟校也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但因为那个年代的特殊性,让更多的人最终还得留在矿山寻谋生计。
但凡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些年考学校真的很难,上线名额很少。像我所在的初中年级有三个班,初中毕业时我和胡小兵考上了中师,黄永华因为是省专业运动队下来的,考上了体师。成绩最好的邓友松报考重庆的重点高中,按照南桐矿务局教育处那年划定的分数线,他差一分而落榜,后来在南桐矿务局一中就读高中,考上了重庆医科大学。还有就是曹德芬在高中就读后考上师专。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其他同学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考起学校。
那时考学校谈不上爱好、理想,纯粹就是找一份职业。好在那时有南桐矿务局技工校,可以解决工作。我初中的许多男同学大多成绩较好,考上了技工校,从而成为矿山的一员。
因为我是农村户口,不能考专门照顾厂矿子弟的技工校,这也注定了我,还有我们兄弟姊妹四人都不能成为矿上的一员。今天回忆起当年的政策,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悲歌。反正我是幸运地考上师范,成为一位普通的教师,至于姐姐、哥哥、弟弟,在后来各自的打拼中虽然艰辛,但也没有遗憾。特别是我弟弟,现在还颇有些资产。如果当年“半工半农”家庭子女可以考技工校,以当年技工校的火爆,跳出农门的急迫,工人光环的招牌,家父对矿山好处的念叨,以及我们几姊妹不错的文化成绩,还真可能也成为矿山的一员,从而走上另外一种人生道路了。
所以我的同学们,他们中多数都有煤矿工作的经历,也秉承了煤矿人的豪气,喝酒、划拳,样样都来。我参加了几次同学聚会,他们总是豪饮,半天都不能散伙。
煤矿工人爱喝酒,当然与从事的高危职业有关。几个同学常自个儿调侃:“万一哪天下井后回不来了,老婆、娃儿,包括家当,全都成为别人的了。所以趁现在活着,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别自己亏待了自己。”一个拿着生命从事的职业,一定有着别人难以了解的内心世界。
后来矿山破产,许多同学不得不拿着微薄的破产费,闯南走北,去寻找自己的出路,有的可能小发,有的仍在创业,有的依旧飘浮。但不管怎么样,常年累月地生活在矿山,工作在矿山,他们身上早已烙上了矿山的印记。
六
想当年,因为地质条件十分复杂,被前来支援的苏联专家建议不宜建矿,后来中苏断交,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力量,排除千难万险终于建设起来,被人们骄傲地称之为“争气煤矿”,并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向国家贡献了几千万吨优质煤炭,有力推进了大重庆的发展,也因此留下数十万人永远的乡愁。
1965年前后,红岩煤矿正式投产。稍上游一点的地方,建设起备战备荒的国防基地——911;稍下游一点的地方,建设起砚石台煤矿。这个原来只有少数土著居住的夹皮沟,瞬间涌入数万开拓大军,开通了客车,修建了缆车,有了学校、医院、商店、食堂、电影院……人烟稀少的夹皮沟,竟然快步进入了工业化的盛境。
可问题是这里没有宽阔的平坝,有的只是时刻得提防的山体坍塌、泥石滚落、洪灾肆虐。勇敢的红岩人抱着人定胜天的乐观情怀,沿着孝子河两岸修建了大量的毡棚屋。一大家子就拥挤在这样简陋的房屋里生活了几十年。豪爽的工友不时来聚会,喝小酒,过人生,简单而快乐。一旦碰上暴雨天,他们就得离开蜗居,以躲避各种不能预料的灾难发生。是啊,稍不注意说不定大大小小的巨石就会从天而至,成为家里的不速来客,滚滚的洪流,就会席卷他们温暖的小屋。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这样的状况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虽然后来陆续修建了红岩工人村、新风井工人村,以及沿河修建了许多坚固的现代楼房,并建设起亚洲最长的缆车来方便大家,这也成为红岩煤矿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但是仍旧有大量的矿工家庭分不到房子,而选择在孝子河边自力更生修建简陋的毡棚屋。
在这里,有解放军因修路而牺牲,有矿工因矿难而捐躯,还有的就是天灾了。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理解那时红岩人的生活信念,不理解是因为没有这种生活体验,而我是出生在红岩的土著,我的生活已经深深烙上红岩的印记,我理解,也必须理解英雄父辈敢于担当责任的宽广胸怀。
既然有争气的煤矿,自然就有争气的英雄。生活在危险的孝子河边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了。谁家的娃儿考上了学校,谁家的姑娘要出嫁了,谁家的老人需要照顾,谁家的矛盾需要排解,都有大家温暖的朝贺和帮助。总之大家融为一体相亲相爱,成为和谐的邻居、乡亲和朋友。
这里一度十分繁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鼎盛。大约在1988年前后,三线建设工厂纷纷向大都市搬迁,红岩911也不例外。我不知道这些三线建设者在离开红岩夹皮沟的时候,心底究竟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留恋?我只知道大家来的时候豪情万丈,热血满怀,为了共和国的事业扎根山区,我也亲见他们走的时候欢天喜地,十分洒脱。
国防厂的搬迁毕竟不是所有家庭,红岩的生活依然在延续。从2011年开始,红岩煤矿的居民领取到万盛棚户改造工程而修建的新房子钥匙后,大规模的搬迁开始了。虽然他们中大多数家庭的居住面积也就三四十平方米,在日益繁华的都市里依然属于蜗居,可我看见他们搬家的时候,脸上洋溢的绝对是满足与幸福。他们将一辈子积攒的家当都搬到万盛城,似乎告别了夹皮沟也就告别了几十年的苦难。
想想,他们将自己的青春,还有后代子孙都烙上了红岩印记,却很少有抱怨和遗憾,有的永远是宽容与大度。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大都市来到红岩夹皮沟,从城里人变为矿山人,一晃就从青葱少年变成了白发老人。
当然,几十年的矿山岁月又岂是能一走了之。有着几十年建设历史的红岩煤矿,在绵延的几座山麓间布满坟蒿。于是在春节前后,在清明时节,已经残败荒凉的红岩工人村家属区重新变得热闹,从四面八方归来的红岩游子到坟上去祭奠故人,到旧居去怃昔叹今,留恋毡棚蜗居,留恋岁月时光,留恋浓浓的红岩夹皮沟情怀。
曾经火红的矿山,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越发困难。一次次改制和破产,让一批又一批矿山人离开。特别是2011年前后,大规模棚户区改造,红岩煤矿工人村、新风井、911、矸子山、垮岩等家属区整体搬迁到万盛新房子社区。红岩煤矿越发萧条。这座修建于1965年的大型国营煤矿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越来越萎缩。但因市场仍然需要大量的煤炭,那些从贵州等边远农村前来挖煤的临时工还是一批接着一批,络绎不绝,让这座拥有光荣历史的煤矿保留着国企最后的荣光。

七
2021年,因为重庆市能源结构调整,红岩煤矿也迎来了关停的命运。昔日的繁华终于烟消云散,渐渐归于岑寂。2021年1月5日中午,我从朋友圈看见矿山的图片,感叹万千,不由信手写了几首打油诗,来以此纪念那些即将消失的矿山,记忆矿山那些美好的人和事。
《从一颗香樟树说起》:一颗葱郁挺拔的香樟/收藏矿乡缘注的情分/五十六年悠长的岁月/储藏记忆满腹的乡愁。一群意气风发的书生/耕耘煤都希望的种子/半个世纪经典的传承/白发见证无悔的誓言。一地懵懂无知的少年/寒窗九年奋发的青春/长大成年生计的奔波/追梦香樟温暖的往事。那株风雨屹立的香樟/装满游子绵长的记忆。
《我和矿山》:那是我童年的乐园/一颗香樟见证矿山诞生/地底光明的采掘/召唤几万人塞满孝河。那是我少年的学堂/一颗香樟见证矿山繁华/上下缆车的脚步/成就几万人憧憬未来。那是我青年的讲台/一颗香樟见证矿山衰老/耕耘沃土的缘分/告别几万人追梦小城。那是我如今的乡愁/一颗香樟见证矿山转型/近乡情怯的忐忑/遥思几万人筑梦幸福。当故乡成为一道风景/矿山与香樟一并都成为记忆。
《老父亲的矿山》:还记得那烹香的保健馒头/是父亲用热血从地底换取/
那列驶向矿井深处的煤车/其实就是追梦幸福的长卷。偎依在井口煎熬等待/父亲用煤黑书写乐观/温暖的澡堂 滚烫的热水/始终牵挂那一斤白干。地心深处的井巷/灰尘飞扬的采掘/落下一生的病根/男子汉的担当义无反顾。单臂驾驭风镐的传奇/迟暮中已成风干的回忆/把酒畅饮的豪迈汉子/注定是煤窑共生的细胞。待到岁月褪去了颜色/父亲与矿山一道衰老。
偶尔我会驾车回到工人村,看着那些断壁残垣的建筑,看着光荣山(又称坟山)那些长满蒿草的坟茔,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那些过去的、未来的,我的,或不是我的人生。
2023年1月28日修改于万盛
(梁光华,现为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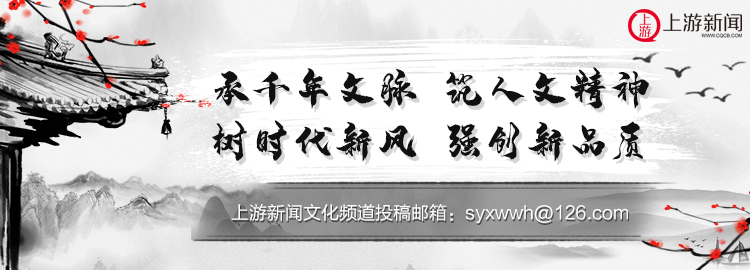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 联系上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