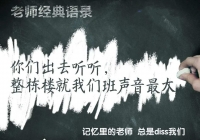崔健发布了新专辑《飞狗》,有人评论说,曾经那个有着生猛批判性的崔健又回来了。但也有人说他过时了,而他自己说“如果说时尚是被操纵出来的,我还是过时为好”。

崔健今年已经六十岁了,鬓角与胡茬上了一层霜。他依然活跃在演出现场,有人建议他每次上台只唱三四首歌就可以了,但他时常一唱就是两个小时,他不感到疲惫,甚至觉得这种方式对他的健康有益,“你做真正喜欢的事,我甚至觉得它是帮助你的器官去恢复的”。
那些他歌曲中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他亦从未放弃。无论时代的大戏唱到哪一出,他就像一根坚硬的钉子,永远牢牢地钉在那里。新专辑《飞狗》发布之后,很多乐迷称,那个最具批判性的崔健,又重新回来了。只不过,这些新创作的歌曲,再难掀起如八九十年代那样山呼海啸般的共鸣声浪。30多年过去,他没有变,只是他赖以成名的那个时代与氛围早已远去。
9月2日,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露天咖啡馆,崔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起他的60岁,他的新专辑《飞狗》,以及他如何面对这个与他成名时已经截然不同的时代。

专辑《飞狗》封面。图/受访者提供
“退休这事儿,
在我的时间表里面不存在”
中国新闻周刊:你今年60岁的生日是怎么过的?
崔健:有人送蛋糕,你没办法,蜡烛也是,有人送的话你就得吹。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来没想过退休吗?
崔健:退休这事,在我的时间表里面不存在。我觉得所谓中年男人,实际上是要工作的。只要你工作的话,你就在承认你自己还是中年。你做真正喜欢的事,我甚至觉得它是帮助你的器官去恢复的。
我现在演出状态比我任何时期都强,我知道在舞台上怎么样调整嗓子,怎么样调整气息,怎么去做大体能的动作。有人说,老崔你一个人唱3首歌、4首歌就行了,你干吗唱两小时?他恰恰不知道,我真正唱完最累的时候就是唱第3首第4首,唱完第4首第5首的时候反而就开始轻松了。你就越放松,你就愿意多动。你越多动,你就越轻松,然后给人感觉他真能闹、真能造。
我周围都是90后的孩子,他们熬不过我。他们累的时候是我看着他们先要休息,完了我还在干活。当然他们睡懒觉也睡不过我。
中国新闻周刊:新专辑的合作当中就有特别老的朋友,像刘元,能有这么多年合作的伙伴是一种什么感觉?
崔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对我有信任,我们在一起合作,能够创造出好东西,而且(他们)也知道我的认真程度。
我也有很多的好朋友不喜欢我的音乐,我反而为这事高兴。因为跟歌迷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一定是有距离的,有人不喜欢我的音乐,然后还接受我的人,说明我的人还挺有意思。
中国新闻周刊:偶像或者歌手,会被歌迷塑造,被歌迷的看法捆绑,你有这种困惑吗?
崔健:列侬不是有一句话说,我们就像是一个不知道去向何方的海上飘的一条船上的旗杆子。在当时西方的摇滚乐最火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要去哪。大家说你就应该是这样,大家都往上去推了,促进他变成这个样子。
我以前早就经历过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拒绝。从第二张专辑,就已经开始挑战这种(捆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流行摇滚,《解决》是朋克摇滚。虽然现在看来,大家还是喜欢听流行摇滚,并不喜欢听朋克。当时我们坚持的表现风格,其实让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种背叛。到了《红旗下的蛋》就更猛了,爵士朋克了,第四张《无能的力量》就开始有说唱。我不愿意复制流行摇滚的路子,并不是说流行摇滚不好,但是我不愿意复制。每一个作品它都是一个生命,它自己会带动你去面对市场,而并不是你主导它的命运。
“摇滚乐批判性的这一面,
我从来就没停止过”
中国新闻周刊:新专辑为什么命名为《飞狗》?
崔健:当时《飞狗》《继续》《时间的B面》这三首歌都在考虑,就征求朋友的意见。几个朋友直接说你不用考虑,就是《飞狗》。《飞狗》亮、响,《继续》太沉重了,《时间的B面》让人还得琢磨一下。
中国新闻周刊:我听说《飞狗》这张专辑创作于一两年前。当时有什么契机吗?
崔健:我写东西以前是积累,现在是集中突然出一批作品。我当时做完那些歌的时候以为一年之后肯定会出来的,结果后期校音校了一两年。我们做了很多实验,达到最后满意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我的朋友圈转发的最多的是《继续》。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和背后的思考,愿意讲讲吗?
崔健:可能里边有一些情绪,大家一听就能听懂。当音乐有了动机,有了和声,有个旋律,他已经就成了一个生命了,你等于是在跟他一起交流。该怎么往下走,怎么磨怎么填词怎么起名,他带着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张专辑,很多人会联想到你早年的一些歌曲,觉得批判性更强。
崔健:我也听说了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有点对(上一张专辑)《光冻》不太公平。《光冻》上来就给你玩一个大的,“光的外面是僵硬壳,它让空气像是监狱”怎么可能听不明白?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制作上,金钱构成过你的障碍吗?
崔健:我一直有演出,我自己通过音乐能够自给自足,也能够雇得起工作人员,也买了很多设备。我买的也不是很奢侈的那种。大公司每年的房租上百万、几十万,我的工作室是自己的房子,也没有这个压力。
我们最大的压力就是扰民,所以我们把隔音做得特别好。我们半夜到早上工作,半夜是可以吹号的,而且不带弱音器随便吹,大声吹都可以。除了不打鼓,什么都可以干,我觉得这是幸福、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工作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养生,因为特别高兴。实际上唯一的压力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是创作中老不满意:听起来怎么就别扭,怎么不对,那就再去学习,再去听别人的专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后,豁然开朗,高兴至极。可是第二天再一听有可能又全都不对了。这个过程就是深一脚浅一脚走过来的,所以耗时长。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是更在意音乐还是歌词?
崔健:音乐,听觉一定是优先的。真的不是文学、文字为主。听觉优先的特点,在摇滚音乐、整个流行音乐范围里边是不可撼动的。其实歌词完全可以让别人作,我就觉得别人作不是独立的风格,比较别扭,就自己能作就作。
我仔细想想我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也是大量的(音乐)实验。1988年,旅游声像出版社那些人相信我,也知道我的风格,占用了他们录音室100天,现在想也挺奢侈的。我能够有机会在录音棚里做实验,尝试各种可能性。
中国新闻周刊:但评论家在解读你的歌曲时,往往是从歌词的思想性上切入。
崔健:我曾经也这么认为。我觉得歌词代表着我一种理性创作的、一种凝聚性的东西,一种气氛和信息。有些朋友,跟我只聊音乐,不聊歌词。像我们乐队的人基本上就是这样。他们甚至很讨厌老聊歌词。另外一帮朋友就恰恰不跟我聊音乐,就聊歌词。
你要说歌词的话,我后期的,比如《光冻》里的,我觉得有记录我心态发展的意义,我自己经常反思这些歌词。但是到最后大家并不接受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听觉上跟我们的语境不太一样,我认为好多东西他们可能感受不到,但这不是听众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写这些歌词的时候,是很直觉性的冒出来去写,还是说它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崔健:理性的,方方面面都要想到的。我写歌词比较慢。有的歌词会一直修改到最后,甚至演唱完了,还要在重新录音的时候再改一遍。我不是那种诗人,一气呵成、一下笔就写完了。有时候也会有瞬间的灵感,后来发现都没什么用。只是记住一种感受,但是用不上。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下一张专辑,已经开始筹备了?
崔健:对,已经开始写歌了。大概什么时候做好就不能说了。我现在有很大的动力想做下一张专辑,就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不满足,发现有很多的遗憾在这张专辑里边。
“如果说时尚是被操纵出来的,
我还是过时为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用歌曲去批判现实社会,它能掀起巨大的声浪,但是现在似乎动静很难再像当初那么大了。
崔健:你要聊声浪,就不要聊作品。声浪不是一个人做起来的,声浪是一个和社会互动的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60后、70后,听说你出专辑,非常兴奋。相对年轻的人,可能就兴趣没有那么大。这会让你感觉不适吗?
崔健: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不听一些很好的音乐。我们成熟了以后,甚至到现在才开始听很多好的古典音乐,体会到古典音乐特殊的那种价值。我觉得年轻人不喜欢听这种音乐,喜欢听一些视觉优先的、有互动信息的、有荷尔蒙反应的音乐。他们喜欢看着帅就行了,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错。我觉得等到一定时候,他一定会产生审美疲劳,那个时候他可能会去找有价值的音乐。
我做音乐的标准是,不要求别人马上听,不要求当下的及时的反应,无所谓。我自己也经常反复听自己的音乐,已经将所谓好听的音乐,筛选掉了。我们把所谓的好听的东西看成是一种油腻。听起来好听,听第二遍的时候就不想再听了,那些东西可能都是讨好市场的,我都会拿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乐评人李皖在《读书》杂志发了一篇文章,叫做《“时代歌手”不再拥有时代》,文中称近五年,已经没有那种既能广泛传播,又精准描摹时代的时代歌曲了,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崔健:说白了就是一帮集体的行业欺诈已经长居在这个市场。他们成为明星,我替他们鼓掌,但是跟音乐没有关系。跟最原始那种、最美好的音乐冲动没有关系。音乐市场有大量的商业行为,全都跟音乐没有关系,百分之零点几的残余剩饭给音乐家而已。剩下的全是大制作,买办团队,买办制作人,甚至开始买点击率,等等一系列的欺诈活动。
如果说时尚是被操纵出来的,我还是过时为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想过根据年轻人的音乐口味,做出一些改变吗?
崔健:我不会改变。但我会潜下心来跟他们聊天。昨天晚上我跟一个19岁的孩子聊,我突然发现他们听的很多的音乐是我没听过的,都是西方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问音乐名字,记下来,开车回家的时候听。年轻人听的音乐比我们这代人听的音乐丰富,非常多元化。
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年代划分的那么清楚,好的音乐就是好的音乐。你要是总以年龄来划分市场的话,里面有很大的误区。首先市场看似是属于年轻人,但是市场是属于一种操作模式,谁符合这种营销模式,谁就能占领市场,市场并不真正代表年龄。
中国新闻周刊:《乐队的夏天》你看了吗?我觉得节目组一定找到过你,让你去当评委。
崔健:我在网上关注过这个节目。参加完《中国之星》就知道音乐综艺节目我是玩儿不转的了。(由于剪辑问题)所有现场观众都知道我在干吗,只有电视观众不知道我在干吗。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你对外界信息的摄入方式是什么?
崔健:我其实跟人交流要少于我自己的琢磨,上网也挺多的。我觉得网络是一个平台,让你去获取平等的信息,但是我仍然觉得现在网络还是受很多限制的,大数据根据你的兴趣所好投喂(信息),有时候也是片面的。我跟很多朋友也发生这样的争论,他们也承认他们自己可能也是被投喂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新的媒介其实是比较适应,比较欢迎新的发行方式。你对抖音、微博这类的新媒介是怎样的态度?
崔健:我不排斥它们,别人给我发了,我自己也有账户,但是我不经常上,因为我觉得大量的东西都是我不感兴趣的。很多朋友也劝我说,你应该利用这个空间去做一些宣传,我觉得这些事不应该是我来考虑。如果我个人考虑,我会发现当我打理这些的时候,它会源源不断地耗尽你的时间,所以我就不碰它了。
原标题:对话崔健:如果说时尚是被操纵出来的,我还是过时为好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