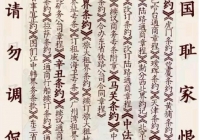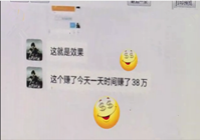新京报重案组37号微信公号消息,3月6日下午,10岁男孩洋洋,被送到雏菊之家。
病房主管曹英把洋洋背上二楼,这是入住的第21个孩子。
雏菊之家,是北京第一家儿童临终关怀病房。临终关怀,或者更准确来说,包括临终关怀服务在内的舒缓治疗(Palliative Care),是指从患者被诊断为可能不被治愈的疾病起,向患者和家属提供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支持和照料,以帮助患者舒缓痛苦,直至离去。
自1987年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机构成立以来,临终关怀服务在多个省份逐渐开展并为更多人所知,这些服务,多是针对成年人尤其是老人,鲜有人意识到,进入生命最后阶段的孩子,也需要专业的临终服务。
洋洋患的是神经母细胞瘤,2月底确诊。洋洋的病情反复,发病时发烧腿疼,小小的身子蜷缩在大床一角,直到医生做完镇痛治疗,才恢复调皮模样。这一幕幕都被徐华和杨琦看在眼里,作为父母,他们将孩子送到雏菊之家,为的就是让孩子在最后的时光能少受痛苦。“不管还剩下多少时日,只想让孩子舒服点。”母亲徐华红着眼眶说。
在洋洋之前,入住雏菊之家的孩子,生命周期最长是40多天,最短仅住1天就去世。生死告别会在某一天发生,但谁也没法算计时日,陪伴,也就成了告别前最好的选择。

▲雏菊之家的墙上,贴着小动物和大树的墙贴。
神经母细胞瘤
噩梦始于去年年底。
洋洋家住山东烟台,年前,洋洋一直喊肚子疼,妈妈徐华带着他跑了当地几家医院,一开始诊断是阑尾炎,但做完阑尾手术,他并未好转。
别无他法,今年2月,徐华和杨琦带着洋洋来京求诊,但诊断结果却如晴天霹雳:神经母细胞瘤。
神经母细胞瘤,最常见的儿童恶性实体肿瘤之一,病情比较隐蔽,很多患者被确诊时,基本到了晚期。确诊那一刻,夫妇俩都乱了方寸。
来北京的这十几天,每况愈下,洋洋已疼得十几天睡不着觉、没法平躺,也坐不起来。疼痛是神经母细胞瘤引发的典型症状之一。
“看他疼得难受,自己也难受。”徐华哽咽。
医生告知杨琦夫妇俩,可以化疗,化疗几十万起步,但治愈率很低,即便效果好或许也仅能再存活一到两年。
看着孩子难捱疼痛,夫妻俩犹豫了一个晚上,最终决定让洋洋入住雏菊之家,“我不管剩下多少时日,就只是想让他舒服点。”徐华眼眶又红了。
洋洋是入住雏菊之家的第21个孩子,他之前的20个孩子,都相继离世。
雏菊之家关怀病房,是55平米的一室一厅,有着淡绿色的墙、白色的门、小动物和大树的墙贴。房间配有高清电视、洗衣机、冰箱和简单的厨房电器,特大号双人床可供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入睡。
“死也不离开这张床。”洋洋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洋洋住进来后,就没出去外头了,Wi-Fi信号足够打游戏。
徐华说,其实孩子很想回去上学,想同学,有一天晚上,他躲在被子里,突然就哭了。

▲雏菊之家的房间内,特大号双人床可供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入睡。
等不到孩子懂事
洋洋的病情反复,3月15日又发烧了。问完基本体征和仔细看了病情后,洋洋的主治医生、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医师周翾叮嘱家属,改用镇痛泵,让孩子自己控制镇痛。
实际上,疼痛管理是临终期儿童舒缓治疗中关键的一部分。没有止痛,就谈不上舒缓治疗的其他步骤。
孩子脆弱而敏感,而临终期的病症和化疗,引起的疼痛其实很大。周翾见过不少孩子,疼痛指数达到重度,孩子没法睡觉,只能无休止地哭闹,让家长与医生几乎崩溃。
经过镇痛治疗,洋洋不疼了,又可以坐起来了。
这是一个清秀的男孩子,长长的眼睫毛、白暂的皮肤,状态好的时候,洋洋能吃能玩,最喜欢玩王者荣耀,最喜欢吃草莓、西瓜。
几乎每天都有志愿者来,陪着洋洋玩游戏、看动画片。在徐华手机视频里,一位志愿者正陪洋洋玩智力拼图,拼图摆了一整张桌子,洋洋不时转头朝着妈妈笑,眉眼弯弯。
志愿者的陪护,并不止是对于孩子,家长的陪护也很重要。志愿者孙阳说,在陪伴家长时,家长心中有情绪,不是刻意去引导,而是让他自然地倾诉,在陪伴孩子时,根据他的状态好坏,他喜欢的活动方式来陪护。志愿者也会引导家长如何陪伴孩子。
入住雏菊之家,也改变着家长与孩子的相处模式,哪怕严厉的家长,也希望给孩子最温馨的最后陪伴。
洋洋期末考试成绩下滑,被徐华骂了一顿,徐华说现在特别后悔。而杨琦也曾因此打过洋洋,所以父子俩关系紧张,很长时间不说话。
杨琦也在苦恼怎么和孩子搭话,这几天,他总坐在外头客厅。
“现在孩子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打他,总得等孩子大一点才会懂,只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谈及这里,杨琦声音有些发抖。
“先陪在一边,总能找到机会搭话。”志愿者孙阳开导他,关键还是在最后一个阶段陪护好孩子,有什么后悔的、还没做的事,要尽快弥补和实现。
杨琦和孙阳谈完,当天下午也坐回卧室里,陪着儿子。
怎么去解释死亡
跟孩子谈不谈及死亡,谈又如何谈?这个问题是很多临终期儿童的家长必须面临的一关。
洋洋的爸爸妈妈,正面临这个难题。
入住了一个多星期,洋洋问徐华“妈妈我住进来还用不用检查”,徐华感觉洋洋仍想做治疗。杨琦说,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这件事,也不敢说,因为如果说了病情,洋洋一上网和看电视,什么都知道了。
周翾教他们,如果孩子问起,可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就说主要现在要准备,养好身体,下一步的治疗现在还没有确定。但不要许诺太多,不要说治好了就回去上学之类,不然会让孩子抱有太大希望。
其实入住第一天,周翾就告诉洋洋,“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问周边的叔叔阿姨。”这是一个表态,周翾是想让洋洋知道,如果他想了解,大人们不会回避这个问题,“不管说不说,没有对错,顺其自然,如果真的要告诉他,就要让他知道,爸爸妈妈会永远陪伴你,不要害怕。”
孙阳也告诉徐华夫妻,家长要保持不回避的态度,如果孩子问起,不要驳斥、不要当作没有这回事,可以问他“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会死呢、你觉得死会怎么样?”,引导他去寻找自己的答案。孩子能接受死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当然是最理想的认知,但孩子不一定能做到,让他去寻找自己的答案,而不是强行把答案给他。
周翾说,对10岁以上的孩子来说,能感受周边的气场和氛围,医生和家长不说,不代表孩子不知道,闪烁其词会让孩子获得模糊信息,反而加大恐惧感和负担感。小点的孩子,不太知道死亡的慨念,更多是希望缓解疼痛。
生活总要继续
4月2日,洋洋的腿又疼了,他的情况在一天天恶化。
病房主管曹英说,为了控制疼痛,镇痛力度正在加大,洋洋已经下不了床了。
看着孩子的情况,某些曾尽力克制的念头,还是出现在徐华和杨琦的脑海中。“没办法的事。”杨琦说,他已经渐渐能接受洋洋将要去世的这件事了。
入住的第三个星期,徐华第一次主动向曹英问起,到时孩子去世,可以如何办理后事。她说想为洋洋助念。
志愿者的陪伴、曹英、周翾的开解,在让家长状态变好、心情开朗,佛乐在房间内徐徐放出,徐华说这让她心情平静,坏的、恶意的东西不会萦绕周围。
曹英觉得,徐华心态变了,刚入住时,她老跟杨琦吵架,杨琦让着她,徐华现在学着换位思考,也不吵了,两人说话心平气和。
这是变得珍惜身边人了。
杨琦说他以前工作、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孩子。现在孩子即将没了,接下来的意义在哪里,他还没想好,但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去更好地照顾在世的、在身边的亲人。
徐华夫妻俩现在都在北京照顾孩子,没了工作,回去之后生活如何开始、怎么过,对他俩来说都还是一团乱,更何况还要直面孩子离去的悲伤现实。徐华说,现在就是先陪着孩子,虽然不知道怎么开始重新生活,但生活总要继续。
(文中孩子、家长均为化名)

▲4月3日下午,雏菊之家的志愿者正在陪洋洋玩游戏。
儿童临终关怀机构送走百余绝症儿童
“缺钱、缺人”成普遍困境
“无法接受孩子疼得死去活来”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此前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增3万~4万名儿童肿瘤患者。
北京雏菊之家的负责人之一于瑛描述,平均每一个小时,就有4名儿童被诊断为恶性肿瘤,最常见的是白血病、淋巴瘤和实体肿瘤。白血病有80%的治愈率,淋巴瘤是50%,实体瘤和神经母细胞瘤还不到10%。
儿童血液肿瘤类疾病“凶险”:发病突然,症状急重,治疗痛苦,花费高昂还难痊愈。
国内的一个现实是,治愈率、好转率、病死率是评价国内医院临床服务的重要质量指标,且三甲医院床位紧张,儿童医院更是如此。
宝贵的医疗资源,首选用于治病救人。当被医院告知无法继续治疗时,孩子的父母只能把孩子抱回家。在生命临终阶段,孩子的身心痛苦、父母的痛苦,再没人能给出专业医疗和心理支持。
“但到生命临终的时候,这些孩子的病痛和心理问题,以及家长的心理问题,会更加严重。”于瑛说。
家长无助心痛,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在离世最后一段时间,遭受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
从业24年、身为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医师的周翾,见过太多这样的人间悲恸。
曾经有一位妈妈求助她,因为癌痛,5岁的女儿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睡。妈妈眼睁睁看着女儿在自己的怀里挣扎,哭声像刀子刺进她的心。
“我一分一秒都熬不下去,觉得自己要疯了。”这位妈妈告诉周翾,一家人熬着挺过每一个夜晚,甚至曾冒出一家三口一起走的念头,“我可以接受孩子的病无法治愈的这个现实,但我不能接受她每天疼得死去活来遭这么大的罪。”
周翾在赴美进修时,接触到了儿童舒缓治疗,让孩子在最后一段时光,过得平静而有尊严,是儿童临终关怀希望做到的事。对临终期的孩子来说,疼痛管理、心理帮助是关键的两部分,孩子的很多症状都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来缓解。
2013年周翾进修回国后,开始尝试为无法治愈的患儿提供舒缓治疗。除了随访北京及周边的家庭,也在网上开设云病房,进行随诊,为回家的家庭及患儿提供远程指导、开出止痛和镇静类药物,并开设舒缓门诊。
起初,周翾进行随访的孩子,病情偏多是白血病,然后其他类型肿瘤的病情增多,周翾发现,随之而来的很多症状无法在家控制,面对面的交流,是更适合服务的一种方式。
建设一间儿童临终关怀病房成了周翾迫切的希望。几经波折,雏菊之家在北京松堂医院设立。
那些临终期的孩子
什么样的孩子需要儿童临终关怀?
在雏菊之家,接收的多是患肿瘤的孩子,而位于湖南长沙的蝴蝶之家,接收的多是患脑瘫、先天性心脏病、脑积水等病症的孩子。他们的共同点,是被医生判定为临终期只剩几个月的孩子。
截至今年3月,雏菊之家送走了20个孩子,平均入住时间为2个星期,而云病房去年随访和随诊的98个患儿家庭,90%都去世了。
与雏菊之家不同的是,蝴蝶之家主要接收福利院16岁以下预期生命在6个月以内的孤残儿童。成立迄今,蝴蝶之家(包括此前与南京合作时)已接收过204个孩子。入住的孩子,会获得护理,有的孩子会在这儿去世,也有的孩子会实现生命体征稳定,这时,蝴蝶之家会为孩子寻找合适的医院,治愈后,他们可能被送回福利院或是直接被收养。
蝴蝶之家收住的孩子,存活率达45%。迄今,112个孩子去世,35个孩子被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家庭收养,29个孩子正在等待做手术。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是国内唯一设置临终关怀病房的儿科医院,病房设立于2014年,此外,近两年各地也开始尝试开展该服务,比方福州协和医院儿童血液科的医护人员,在2016年组建了福建第一支专业舒缓治疗团队。
实际上,面对国内儿童临终关怀的需求量,目前已经设立的几个机构和团队,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
蝴蝶之家负责人符晓莉说,2015年有个数据,全球对儿童临终关怀的需求量是2100万,经换算,中国是450万左右。
巨大的需求和零星的机构之间,儿童临终关怀服务存在巨大空白。
并不成熟的临终关怀体系背后,各机构也在探索和形成自己的模式。
从2013年开始尝试为病人提供儿童舒缓治疗,周翾在摸索着完善服务。她对整个舒缓治疗的模式设想,包括疼痛管理、临终关怀、心理辅导以及为孩子开展活动。
疼痛管理包括开设舒缓门诊,开展对家长、医护的培训课程;临终关怀包括儿童临终关怀病房(即雏菊之家)、云病房随诊、入户随访;心理辅导包括哀伤辅导,以家庭为单位一对一进行辅导;为可治愈的孩子开展活动,由儿童治疗舒缓活动中心组织。
而符晓莉认为,真正实现儿童临终关怀的理想模式,应是“全人、全员和全程”。其中全员不局限在关怀临终孩子,还要关怀孩子身处的家庭,全程则应该是在孩子病情被发现时,即接入服务,可治愈者获得服务后,继续进行治疗,不可治愈者,则获得服务,在生命最后一程,获得平静和尊严,最后离去。

▲蝴蝶之家位于长沙第一福利院的幸福楼2楼。
患儿家长的艰难抉择
即便如此,儿童临终关怀,也很少被人关注和了解,即便是一些患儿家长,也不会选择这项服务。
周翾在北京儿童医院开设的名为“舒缓治疗”的门诊,往往会接收到肿瘤科别的门诊转介过来的家庭。当医生判定自己的病人不可治愈时,就会推荐他去舒缓门诊。
接待家长时,周翾必问的一句是,“是否准备好不再接受治疗”。
实际上,大部分家长都是初次接触“儿童临终关怀、舒缓治疗”这个概念,有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就符晓莉在蝴蝶之家与湖南省儿童医院合作新设的门诊中与家长接触感觉,有的家长会产生误解,拒绝接受,进而过度治疗。
以此为前提,有的家长会愿意接受服务,也有的不死心,仍希望继续治疗。即便治疗已不太有意义,存在风险和痛苦。就于瑛所了解,在舒缓门诊开了吗啡、进行镇痛治疗之后,孩子不喊疼了,状态好了,看起来又有了希望,家长会想继续找治疗的方法。
无论孩子和家长做出哪种选择,周翾都表示尊重,支持并相信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同时,她会告知后者可能会出现的状况,让对方更好做考虑和准备。
去年有个入住雏菊之家的家庭,仍不放弃可能的治疗。妈妈一直陪着孩子,而爸爸一直在外奔波,打听可能的治疗方法。孩子去世那天下午,爸爸正在外奔波,妈妈电话打来让回来,“孩子不好了”。爸爸赶紧回了,没一会,孩子就走了。爸爸事后特别懊悔:“我瞎跑什么,我应该安安静静在这儿陪孩子,这几个钟头再陪一陪。”
周翾见过很多次,在家人面前没有表露情绪的男家长,却在她的诊室里哭泣,诉说他承受的压力,还会问:我给孩子做的这些决定是对的吗?
去年有个入住雏菊之家的家庭就是这样。全家人都反对,只有妈妈执意让孩子住进来。第二天妈妈再度犹豫了,心里犯嘀咕,忍不住问于瑛,“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吗?孩子会不会其实还有治愈的希望?有听说治愈的吗?”她怕自己的一个决策错误,决定了孩子不同的命运走向。
选择背后有巨大的纠结,但关键是不想让孩子再痛苦。周翾说,愿意接受服务、选择不再让孩子进行高强度的治疗和无谓的抢救,家长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不是钱,是让孩子平静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无偿医护与资金众筹
雏菊之家历经坎坷,病房最终在2017年底建成。舒缓门诊、哀伤辅导、随访数据库也在近几年先后开设。
同为雏菊之家负责人的于瑛说,雏菊之家目前最迫切的愿望是多建几间病房,“目前只有一个房间,去年有好几个家庭,没能等到入住就去世了,让人很遗憾。”
新建病房,资金是最大的难处。一直以来,周翾开展儿童舒缓治疗服务,基本靠“众筹”。
2014年,她成立了新阳光儿童舒缓治疗专项基金,基本每年儿童治疗舒缓活动中心和雏菊之家需要资金,都是通过基金在向社会发起募捐。于瑛作为中心的负责人,每年都在为房租、活动经费、人员成本等各项支出烦恼。
人力也是难点。医疗团队目前21人,大部分是来自儿童医院的医生护士,但大家都是兼职、无偿在做这件事。
周翾身兼数职,凭着个人热情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忙得周转不开。于瑛说,有时两人约好晚上11点打电话,她得等到12点后才能打通,因为11点多的时候,有孩子家长打电话给周翾。
曹英去年加入雏菊之家,作为有多年经验的护士,有力支持了雏菊之家的运营,而出于资金和人力的缺乏,曹英拿着低于市场价的工资常常加班,虽然甘愿,却让于瑛很不忍心。于瑛很希望今年能实现为无偿、低偿投入服务的工作人员给予补贴。
行内人士的共识是,目前儿童临终关怀在国内的困境,主要在于大众不了解、政策无支持、资金来源不可持续。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认为,目前儿童临终服务模式没有统一标准,虽然近几年各地基本都是自己在探索,也形成了总体框架,但很多细节都没做好,包括哀伤辅导、殡葬等服务,迫切需要专业人员投入。
而这些,也依赖资金投入。据了解,国外资金来源主要在四方面,包括政府资金、企业捐助、项目支持和家庭捐助。
资金来源不可持续实际上是儿童临终关怀服务最大难点,刘继同表示,这与政策上没有解决定性和责任承担有关系。据了解,儿童临终关怀从注册到开展服务,国内都没有相关的政策。
前几年,业内一直有声音支持儿童临终关怀应纳入卫生制度和医保,但刘继同发现,操作难度较大,从妇幼健康角度入手开展服务或更有实操性,也因此正发起尝试。

▲3月20日午饭后,蝴蝶之家的护理阿姨正在哄孩子睡觉。
已经起步的临终关怀体系
虽然儿童临终关怀目前存在认知、专业人员及资金投入等问题,但国内对儿童临终关怀服务的推动、认识比前几年进步了很多,这是行业内人士的共识。
符晓莉希望,在国内儿童临终关怀这个全新的领域,推动发展,制定一些行业标准,同时引进更多专业技术资料,推广儿童临终关怀理念。
为此,蝴蝶之家拍摄了国内第一个儿童舒缓的纪录片,并于2015年发起举办首届中国儿童舒缓护理研讨会,与各地医院医生交流,进行国内现况分析和探讨,大会迄今已经举办了4届。
2017年底,周翾还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儿童舒缓治疗亚专业组,组织培训来自多个省份的医生护士。
除了周翾和符晓莉各自在推动培训和探讨,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儿童临终关怀与家庭卫生保健专业委员会”也于2018年成立,周翾和符晓莉均是会员,刘继同则是首任主任委员。
刘继同介绍,委员会是全国国家级专业协会中首个二级专业委员会,首个儿童临终关怀(舒缓医疗、安宁疗护)与家庭卫生保健专业委员会成立,相当于填补中国儿童临终关怀与家庭卫生保健专业服务国家空白点。
周翾觉得,国内儿童临终关怀领域的进步,不乏因近几年成人政策的推动,儿童领域是“搭了便车”。亚专业组的成立,意味着儿童舒缓治疗正式被认定为一个亚专业学科,而且目前多个省份已经有医生护士参与过培训,保证了将来每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能有一支儿童舒缓治疗专业团队。
谈及儿童临终关怀时,刘继同提到一点,目前国内临终关怀发展多年都难被接受,更别提儿童临终关怀,这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出于国人的生死观。
而对于儿童的临终关怀的意义,蝴蝶之家办公桌上所贴一句话,或许可以解释: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不管生命是长是短或是否为社会做出贡献;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被爱、被关怀,以及在爱和尊严中离开。

原标题:等待死亡的第21名孩子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