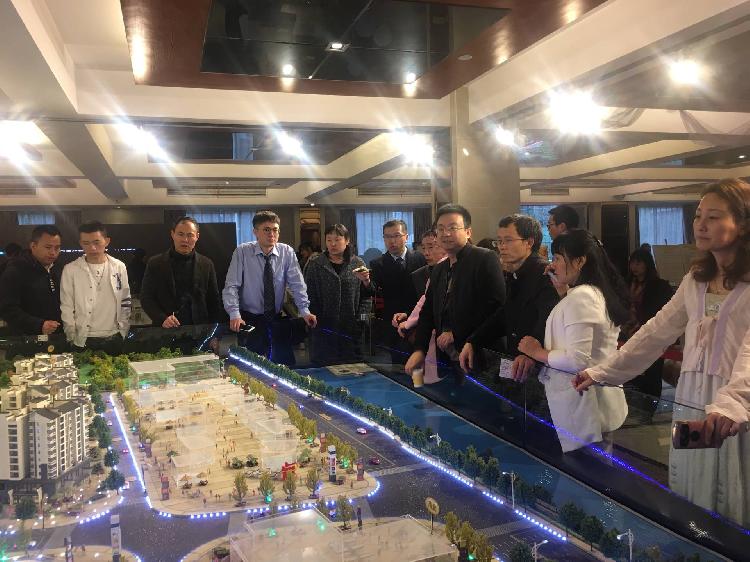老人扛着锄头走过“状元村”小广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影
新京报消息,“这个是1978年考上清华的,他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现在是教授。这个是山东大学的博士后,这个是硕士……”洼里村会计彭淑禄手里,有一本打印的红色小册子,这些年来,所有走出村庄在城里安家落户的人,都在上面。
洼里村原来叫彭家洼,村里320户、960多人,绝大部分姓彭。这个泰山脚下的村子,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农耕废弛、人员流失,走在村里,好半天才能见到一两个老人慢慢悠悠地经过,几乎没有年轻人留在村里,哪怕当下正春耕季节,也没有一点点繁忙气象。
如果只是走马观花一般地路过,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村子还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小小的村庄里出了9位博士、9位硕士,将近60位大学生。

主任彭乐冬说,以前县太爷经过洼里村都会“落驴”。
状元村没有状元 老校长借钱供孩子上学
几年前,因为当地媒体一次偶然的报道,洼里村有了一个“状元村”的称号,其实洼里村没有高考状元,无论是任何意义上的状元都没有。之所以被称为“状元村”,是因为这里走出去了数量远超其他村子的大学生。
这个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村子,曾经以出教书先生而闻名,据村主任彭乐冬说,以前县太爷下乡,经过洼里村的时候,都会主动“落驴”,以示尊重。
这个传说无从可考,洼里村也没有 “下马石”“落驴石”之类足以证明传说的东西留存,村主任讲这个故事,似乎想证明,洼里村的尊师重教是有传统的。但在村里小学的老校长彭西庆看来,之所以拼命读书的原因只有一个——穷。
彭西庆的儿子,是中科院的博士,他至今还记得当年供孩子上学的艰难,那是1992年,儿子考上师专,入学时要交700元,此时的彭西庆,已经当了12年小学校长,经济条件在村里算好的,但依然拿不出700块钱,东拼西凑才借齐,后来小儿子又进入山大读本科,还要交1200元,彭西庆不得不再借一次。

老校长彭西庆夫妻俩正在剥花生。
老人苦点就苦点 孩子们再不能受穷了
洼里村是典型的农耕村落,村里人世世代代种地为生,虽然东临泰山,但实际上,离泰山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泰山的旅游业,几乎不可能辐射到这个村子里,村里西面有一条河,叫做淘河,是汶水的支流,但远没有出过大汶口遗址的汶水那么有名。
那山那水,对洼里村来说,都是靠不住的。和传说中的“教书先生之乡”相比,它还有一个更有可信度的称号“建筑之乡”,这是无数村里人出外打工,在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上“拼”出来的。
彭兴坤已经60多岁了,仍旧在外地打工,超过了55岁,建筑工地就不要了,极少的看门、看料场之类的工作,都得是老板的熟人才能干。彭兴坤只能到处打点儿零工,“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彭兴坤的妻子说。
彭兴坤的一儿一女都是大学生,女儿读博士,去年刚刚毕业,在一所高校任教,儿子去年本科毕业,已经工作。对彭兴坤一家人来说,千斤重担算是放下了,“比起以前,好多了,至少没有负担了”,彭兴坤的妻子说。
彭兴坤的妻子不太愿意谈及那些年的艰苦,也不觉得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村里只要有孩子上学的,谁不穷呢”?她的观念很朴素也很现实,“穷才要上学,我们这一辈人,苦点儿就苦点儿,孩子们再不能受穷了”。
孩子第一年生活费靠贷款 好多年才还清
彭兴坤的侄儿告诉记者,彭兴坤的孩子考上大学后,夫妻俩掏不出孩子的生活费,甚至在村里也借不到足够的钱,最终还是靠贷款,才能送孩子去上学,“学费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孩子在学校也能勤工俭学,但一开始的路费、生活费之类的,就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们自己哪儿能贷出来款,什么抵押也没有,还是托人担保才贷到”,彭兴坤的妻子说。前前后后,彭兴坤一家贷了6000元到7000元,一点点还,还了好些年才还清。如今,彭兴坤在外打工,两个人的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但也仅止于此,“也就是能生活吧,只是不用再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在老校长彭西庆家里,夫妻俩正在剥花生,这是今年的种子,早年民办教师转正时,他们家里几乎就没有地了,仅有的一点儿地,种点儿花生之类,权作消遣,他的退休金足够他们老两口生活。孩子们都在城里成家立业了,偶尔回来,也不会再去地里,他们已经彻底和土地告别了。
彭兴坤在外地打工,一年难得回家,儿子过年过节才会回家,大部分时候,都是妻子一个人在家,唯有女儿,在一所师范学院教书,寒暑假的时候回家和母亲住一段时间。彭兴坤的妻子也会担心女儿的婚事,“都30岁了,着急,可着急又有什么办法呢,孩子在城里,我们够不着”。
留在乡村的老人们,确实很难再为进城的儿女们负担更多的东西了,成家、买房子,这个城里的父母操心的事情,基本上都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洼里村的老人们。
他们崇拜学历 但并不真的了解学历
从彭兴坤家里出来,记者碰到了一位刚要出门的杨大姐,杨大姐的丈夫在广东打工,留下她在家里照顾上学的小儿子。
杨大姐的儿子还很小,在隔壁村上幼儿园,每天早晚都要接送,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她希望孩子毕业后,接着考研究生。“学历低了不行,找不到好工作,硕士都不行,最好是博士”,她说。
或许是因为考出去的大学生足够多,也可能是村里重教的风气所致,许多村民都很重视学历,希望自己孩子的学历越高越好。但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了解学历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会觉得博士后比博士的学历要高,留美的博士比博士后还高,有时候也会把山东大学和济南大学弄混。村里面走出去几十位大学生,但他们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中科院等极少数几个名字,大多数孩子究竟考了哪个学校,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的家人才能说得清。
不仅是杨大姐,村里的人们几乎都有着类似的观念,学历高了才好找工作。这样的逻辑简单而朴素,就是彻底离开穷困的乡村,而要想走出乡村,考学要远比打工好得多,“打工也行,但那是青春饭,就干那么几年,老了还得回来。而且现在结婚要房子、要车,得打多少年工才能赚到。考学出去就不一样,最起码工作轻松,不用风吹日晒,老了也有保障。一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

蓝天下的洼里村。
合欢树已经如盖 小学没有了
洼里村的小学,改革开放后,经历过三任校长,彭西庆是第二任,第三任叫彭淑德,如今也已经退休十多年了,村里的小学,也早就撤销了,如今改成了村委会。
唯一还和当年的小学有关系的,只剩下院子里的两棵合欢树。
彭淑德现在还记得,合欢树是1978年栽的,那时候他还只是个教员,如今,40多年过去了,合欢树已经高耸入云,树阴遮住了小半个院子,但当年的故事却已经模糊不清了。彭淑德甚至想不起来,他教过的学生中,到底有多少考上了大学。
“村里人太少了”,村主任彭乐冬说,以前每年都有二三十个适龄学生,如今也就五六个,“开不了一个班了”。
现在,洼里村的孩子们,都去隔壁村的小学上学,那是一个大村,有两千多人,周边五六个村的孩子,都在那儿上小学。
中学则要到乡里去上。杨大姐的女儿,就曾在乡里上中学,每两周回家一次,“那时候连公交车都没有,附近村里有大车的人家,定期接送孩子们,收很少一点儿钱”。后来,县里的中学招生,杨大姐的女儿看到后,自己跑去考试,被录取了,上学也就更远了。

村民正在种树。
没人种地了 都种白杨树
尽管洼里村的大学生很多,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考上大学,考不上的,只能出去打工,“年轻人们不会留在村里,更不愿意种地”,彭乐冬说。
村里的大部分地,都改种白杨树了。杨木质地疏松,不算是好的经济树种,甚至无法直接成材,村里的白杨树,长成后都是卖给附近的板材厂,板材厂切削、粉碎之后,直接压成复合板。但从经济效益上看,还不如种粮食。
唯一的好处,就是它几乎不用看管,“七八年就可以卖了,中间很少需要照顾,人们可以腾出时间去打工”,会计彭淑禄说。
对干不动农活的老人来说,白杨树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只是不能以此为生,“真的老了,还是要靠孩子,地里的产出,补贴点儿还成,靠不住”,彭淑禄说。
彭淑禄也已经70多岁,从198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村里当会计,村里的经济情况,没人比他更了解。“我们这个村,要发展起来太难,没产业、没项目、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特产。村里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学”。
走在村里,路上背柴的、打水的,骑着电动三轮的,几乎都是老人,村里唯一的小磨坊,几个年迈的老人,正在这里粉碎饲料,材料是花生壳,在粉碎机上粉碎之后,可以喂猪、喂鸡、喂狗。除此之外,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发出声音的地方。
好好学习 就是“状元们”最好的建议
考学出去,意味着个人命运被彻底改变了,但村子还是那个村子,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出去的人偶尔回来,也帮不上村里什么忙,有时候他们也会给村里一些建议,但最好的建议,就是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彭淑德说。
走出去的学生们,对于日渐凋敝的故乡,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已经博士毕业两年,在一所大学里教书的彭淑庆说,“我们村里出来的学生,很多都在学术方面发展,都没有太大的能力帮助村里”。
1993年,彭淑庆小学毕业,进入中学,要到乡里上学,“那时候国家经济已经不错了,但村里还是非常穷,我和哥哥两个人上中学,每周生活费加起来也就2、3块钱,这点儿钱,不用说在食堂吃饭了,就连馒头都买不起。仅有的2、3块钱,用来买圆珠笔芯、本子都很紧张”,他说。
兄弟两个人只能从家里带煎饼、咸菜充作口粮,“夏天不能带太多,爱坏,冬天冷,煎饼都冻硬了”。考大学时,彭淑庆选择了一所师范专业,只因为每个月有70块钱的补助,靠着这些补助,加上勤工俭学,才能勉强完成学业。

曾经的茶店如今大门紧锁。
专家观点
吸引人才的方式,不是靠情怀
上大学后,彭淑庆就很少回家了,假期要打工,唯有过年,还能回家待几天。工作以后,回家的次数也没有变多,“虽然有寒暑假,但自己有了孩子,要照顾孩子”。
逢年过节回家时,村里有考大学的孩子,也会向彭淑庆求教,“也想给村里做点儿贡献,但力量实在微薄,只能在学业上给孩子们出出主意,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办法”。
在谈起洼里村的振兴时,村主任彭乐冬有些无奈,“还是要靠产业扶贫,但资源太少了,也就背后的那条河,整理整理,可能还会有点儿游客”。
但即便这么一条河,也不是洼里村独有的,村主任的振兴计划,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依旧不可知。“这可能是很多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中共同的困难”,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阳说,“任何农业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都是以人口大规模流失为特征的,完成转型的标志,不是人口回乡,而是生产模式的转变”。
出外的大学生,他们比村民更有知识、眼界,但同样抵挡不住传统村庄和传统农业的衰落,“我们还处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直到今天,考大学依旧是很多农村孩子摆脱贫穷、迈向中产的最好途径。他们考上大学,不仅是从乡村走向城市,更是身份的变化,他们有了干部身份,可以考公务员,可以进入大企业,可以不断地晋升,这是迈向中产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城市人,不再是村里人,想要回报乡村,非常难”。
学生们出走之后的乡村,又该如何振兴?杨阳认为,“还是要依靠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转为相对集约化的现代农业。至于人才的问题,乡村振兴也好,现代农业发展也好,确实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但吸引人才的方式,不是靠情怀,而是靠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支持,让愿意去乡村的人,可以得到和城市相同甚至更好的待遇,比如住房、保险、养老等。人才的流动一定是自由的、也是自愿的。只要乡村确实有吸引人的东西,且没有后顾之忧,自然有大量的人会去乡村发展”。

年轻人不愿留在乡村。
记者观察
不回乡的学子 和乡村渐行渐远
不过,今天的洼里村,离人才的自由流动还很远。
彭淑庆的求学经历,或许是这个村子里所有大学生的一个缩影,他们走出了乡村,也从此和出生、成长的乡村割裂,除了偶尔回乡探亲,几乎不会再和乡村发生联系。
考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没有改变这个村子的命运,甚至因为人口的流失,反而加快了乡村的凋敝,这个本来就很小的村落,还在进一步萎缩,变得更小。“我们家有六口人,但户口本上,只有三口人”,会计彭淑禄说。彭淑禄的儿子在城里安家落户,户口还在家里,但儿媳妇、孙子孙女的户口都在城里。
在彭淑禄的眼里,家里有他们老两口、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六口人,但户口本却只有三个人。洼里村320户,只有960人,平均每户三人,那些连带着户口一起离开的人们,他们的身份,不再是村里的居民,而是走出乡村的第一代移民,或许,他们逢年过节还会回村,因为村里还有他们的亲人、记忆,但到了他们的孩子乃至孙子那里,乡村就只是一个字典里陌生的词汇。
离开洼里村的时候后,已近日暮。车行减远,村庄在大片的白杨树林里若隐若现。忽然觉得那个安静、空旷的村子,就如那些白杨树一样,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只能拼命地挤压自己,才能变成板材,变成家具,远赴他乡,供给人们使用。留在原地的,只是一片光秃秃的树桩,就像大地上的一个个伤疤。
原标题:培养出18位博士硕士“状元村”却老得走不动了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