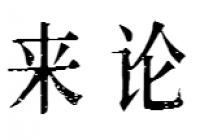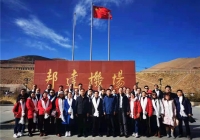南沙河村,位于陕南山区,没有光滑的地面可以让滑板鞋摩擦,只有布满青苔的泥路,留守的妇女的和老人。
庞麦郎,是这里唯一的年轻人。
他是“大明星”,但已不属于城市,一路从北京退到深圳、从上海退到杭州,从温州退到成都、从东莞退到西安,退到泥土、草木,直到退无可退。
他亦不再属于村庄,整日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与他人沟通,发病的时候,轻则发出一声急促的“滚”,重则摔家什——家里拿来冻肉的大瓷碗就是被他摔烂的。
邻居说,他心里有“气”,需要发泄。
事实上,他病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拯救自己》
一瓶没喝完的山楂饮料立在窗台上,瓶子上印着生产日期:2021年2月6日。
自从生病以来,庞麦郎胃口很差,一碗米饭,扒拉来扒拉去,半碗都吃不完。他只想喝饮料、吃零食,实在要吃饭,就拿豆瓣酱拌一下,菜不要,肉也不要。
母亲说,“我做什么他都不爱吃,都不好吃”。
据她称,儿子大约四年前就生病了。病情于去年底加重,除胃口不开,睡眠也不行。有时夜里庞父上厕所,发现儿子在家里转来转去,“好像时间还长”。
他情绪上来,轻则发出一声急促的“滚”,重则摔家什——家里拿来冻肉的大瓷碗就是被他摔烂的。邻居说,他心里有“气”,需要发泄。
庞父决定把他送往医院。待儿子工作返乡后,他扯个谎,说外来返乡人员需要做核酸检测,地点在大安镇。就这样,他把儿子带到位于大安镇的宁强精神病康复医院。医生检查后告诉他,是精神分裂症,还说病得有一段时间。
第一次入院以逃跑结束。庞父说,三天后,有人给病友送饭时忘了关门,儿子得以从医院溜出来,先回家,后赴西安直播,直至大年三十回到老家。
3月1日,家人再次将他送往医院。
据庞父的说法,那天他发现儿子不对劲,眼睛鲜红。红的时间太长了,他跟妻子说,“今年,抓紧时间治疗他”。他给村支书打电话,让后者把医院救护车叫来,后来村支书叫来医院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
人们来到时,庞麦郎正在房间里。父亲说,今天要看病咯。儿子问,在哪儿?庞父回,大安。“我不去,我没得病。”儿子说。
“你考虑下子。你想想看你以前的做法。如果你还头脑清醒的话。你考虑下,车来了。”
儿子答应了。
前来的工作人员把儿子的手别在后头,用胶带绑着。庞父看得难受,上前说,“师傅,不要这样绑着,他不是坏人,你这样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把儿子送到医院后,他看着儿子悲从心来,“我发现我们两个,好悲惨了”。
或许出于保护儿子的态度,后来再被问起时,庞麦郎的父母对打人一事一再否认,他们坚称只是做了下样子,“没打着人”。
一位邻居告诉九派新闻记者,他曾从庞父口中听说了被打的消息。那天他们在厨房里烤火,庞麦郎打了庞父一下,“没打他妈。(伤情)没咋样,打得不咋样。”
庞母称,有时儿子发火后会跟她道歉,“妈妈对不起,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的父亲是瓦匠》
3月中旬,南沙河村的油菜花长势良好,没过人腰。正是春耕的季节,庞麦郎的父母踩着解放鞋下地干活,加上承包的邻居家的,有七、八亩地要犁。
庞家手扶拖拉机轮胎前一天爆了,到镇上买新的估计得300块。庞父已好几个月没收入,过年返乡后,他今年不准备再去打工,要在家守着,把儿子的病治好。
庞麦郎还有个哥哥十多年前入赘到了山西。和村里许多孩子一样,他的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在家种地。
在邻居们印象里,庞家父母都是本分人。一位邻居称,庞父“是个务正业的人”,没有赌博之类的不良嗜好,赚来的钱都拿来维持家用,平日里乡亲们种地有需要帮忙的,他也都帮忙。
庞父63岁了,小学二年级的文化程度,早年天南地北地下过煤矿。
一位村民记得,80年代和庞父一起在煤矿里推车,一天忙活下来,赚2块钱。他还做过瓦匠,庞麦郎写了首《我的父亲是瓦匠》,“夜幕下的路灯,夜幕下的背影,夜幕下的瓦匠,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近些年,庞父的工作是在工地上打混凝土。另一位和他一起打工的村民说,“打混凝土可辛苦”。老板规定了干活的面积,要干完才休息。白天干不完就夜里干,夜里干不完就白天再干,连续工作个十来二十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工资按小时算,1小时10来块钱。
打混凝土的时候最怕下雨,套着雨衣,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冬天,手冻得慌也没办法,只能放在腋下暖和暖和。
辛苦归辛苦,现在,庞父连这样的工作都快找不着了。前阵子,他给太原好几个地方打去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60岁以上就不招了。他已63岁。
外出打工,庞父一年在家的时间不过两三个月。当被问及如何教育孩子时,他回答,“教育的时间太少了”。
陪在孩子身边的是不识字的母亲。她是个无法停歇的人,要下地锄草、收割,山坡上高高低低的七、八亩地,够她跑个遍。干完农活,还要生火、做饭、打扫卫生……不得闲。她比丈夫大一岁,拍着肩、颈、背、腰,“这也疼,这也疼”。
夫妻俩忙着生计的时候,儿子慢慢长大,上中学,上职中,然后去了外边的世界。2008年的某一天,他从广东打工回来,说不想再打工了,他要写歌。
有记者问,知不知道滑板鞋是什么意思。庞父回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他只是关注着短视频平台上的儿子的消息,看着一曲唱罢,台下的欢呼声是否够热烈。若人不多,掌声平平,他看到儿子脸上写着沮丧,心里也一紧。“干他们这一行,压力很大”。
从去年开始,哪怕在家,庞麦郎也把卧室门锁上。庞父不明白儿子为啥要锁门,对儿子说,我们还要取东西。儿子说,你要取啥,我帮你就是。
《古镇里的怪兽》
演出一直赔钱,2017年,庞麦郎退租了西安三室一厅的房子,告别了那个可以俯瞰西安城的落地窗。他回到汉中老家居住,有演出再出去。
乡村生活看起来是寂寞的。他的老家,汉中市宁强县代家坝镇——那个他自称为“加什比克·汉克顿尔·古拉格”的地方——离县城16.5公里。
村庄名叫南沙河村,据说因为那里位于河流下游,河里有泥沙堆积起来。从县城到村子,要从大路转小路,再转更小的路,在不过5米宽的盘山公路上转过一个又一个弯,耗时约1小时才能到达。
这里是庞麦郎一直拒绝曝光的家乡,他苦心经营着一个“庞氏骗局”:对外宣称叫庞麦郎,90后,出生于台湾基隆。
但实际是,原名庞明涛,小名“军娃儿”,1984年出生与陕西,父母是地道农村人。
还有一位与庞家相熟的司机记得,庞麦郎每次出门,哪怕只到镇上,都会戴上帽子和口罩。
其经纪人白晓解释,“他会觉得公众人物就应该有很好的生活、很好的家庭,但他下了舞台一转身,是一座大山,一个破旧的房屋。这是他在做自我保护,当然这跟他生在骨子里的自卑是有关系的。”
庞家在的这片区域只有8户人家,剩下的7户都和庞家一样,男人打工,女人务农。
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这里只剩下几个老人,包括一个70岁的坐家女,和一个耳朵听不清的老太太。
庞麦郎与这里格格不入,因为他是村庄唯一一个年轻人。他离群索居,在陋室里构筑自己的世界。
从去年开始,哪怕在家,庞麦郎也把卧室门锁上。庞父不明白儿子为啥要锁门,对儿子说,我们还要取东西。儿子说,你要取啥,我帮你就是。 吃饭时,庞家的猫跃上了桌,它已经8岁了。庞父笑着说,明涛把这猫惯坏了,给它喂零食喂饼干,猫现在有点挑食。 猫还有些怕生,每当生人靠近,惊慌一颤,转身闪进了黑暗里。
多位邻居告诉九派新闻记者,村庄里和庞麦郎一样年纪的孩子,男的外出打工,回来结婚生子,女的也出嫁了。“他快40了还没成家,父母也一定很着急。”
但是,庞麦郎一度也是父亲的骄傲,“整个南沙河村,就他念书的时间最长。”
父亲说,这里的孩子多半初中都没念完,而他家的娃,读了初中、职高,还上了西安外事学院。
《我将停留在哪里》
庞麦郎入院3天后,父亲偷偷去医院看他。
为了省钱,他坐大巴到大安镇。医生说现在刚送进来,最好别去看望,免得让他情绪激动。
庞父问医生,要是不配合治疗的话,你们怎么处理他?医生回答,那就用胶带缠他的手。
3月13日,他又去了医院,医生说儿子恢复了很多,可以见面了。
庞父担心影响儿子恢复,没跟儿子见面,只是隔着玻璃远远望着,儿子坐在床上,脚随意地晃来晃去,看起来有些闷闷不乐。
他希望今年把儿子的病治好,要是镇上的医院治不好,他谋划着把儿子送去更好的医院。
眼下,庞麦郎给村里子里带来的更多是困扰,村干部宣称接到全国各地无数电话,“再这样下去,我和庞麦郎他爸都快被逼成精神分裂症了。”
庞父对媒体没有太多认知,只能反复叮嘱蜂拥而来的记者,对孩子手下留情,因为也有人打招呼不让他再接受采访,免得儿子出院后看得伤心。
毕竟,庞麦郎的确被一篇报道伤过。
等儿子出院,他要问问儿子今后如何选择,若还是做回歌手的老本行,他拜托记者们今后多多关照。“靠你们了,不然他这辈子就完了,不可能再成功了”。
门外,庞家养的大白鹅梗着脖子,向田野嘎嘎直叫,每一声都一样,又不一样。
注:《拯救自己》、《我的父亲是瓦匠》、《我将停留在哪里》系庞麦郎的单曲名;《古镇里的怪兽》系庞麦郎专辑名
原标题:村里唯一的年轻人庞麦郎被绑着送医,父亲:不要这样绑,他不是坏人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