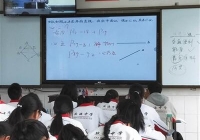盐源中学直播班上课的实况。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消息,我的家乡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四川教育界,甘孜、阿坝、凉山三州是著名的教育落后地区。2013年高考,我所在的班级,是全州下辖17个县市里成绩最好的文科班,最终也只有十多个人上了一本线。
2018年12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文章《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我忽然想起了高中教室对面,那个总是拉着窗帘上课的网络直播班。
那是比我们低一年级的文科重点班。每堂课上,讲台中央的投影屏幕,同步直播着成都七中的课堂实况和教学PPT。为了投影效果更好,他们班总要关上灯,拉上窗帘。
当时常听网班的学妹说,成都七中的试题太难,熬更守夜都写不完。因为没空洗头,她的刘海总是油得一根一根的。
在凉山州冕宁中学2019级高三直播班班主任王学语看来,从2002年凉山州探索直播教育开始,17年来,直播课已经成为一些县城学校的金字招牌,但它并不是解决贫困地区所有教育问题的“万能药”。
“对于偏远山区的孩子,直播屏幕是一座沟通优质教育资源的桥梁。”王学语说,“但直播只是一项技术,一块屏幕背后,最重要的是人。”
一块屏幕的两端
这个春节,我从州府西昌出发,分别乘车几小时去往冕宁县和盐源县,探寻那里的直播教育。冬日里的大凉山,艳阳高照,一路上弯道盘根错节,山风呼啸,路上时有暗冰,地里的苞谷秆子已是枯黄一片。
大凉山中的冕宁中学,是成都七中第一批5所网校中的其中一所,2002年,因为得到“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的支持,开始尝试免费的直播教育。

2月1日,四川省冕宁中学原址,雄鹰雕塑寓意着教育帮助学生飞向蓝天。新京报记者付子洋 摄
从最初到成都开会讨论直播事宜起,要不要上直播课的争议,便一直存在。许多从前在讲台上激情洋溢的老师,忽然觉得自己成了配角,难免心生抵触。
“最终说服大家接受直播的理由是稳定生源。当时我们的学生老往西昌跑,好生源很难留住。”王学语说,他是最早一批带直播班的老师之一,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头几年的实验,确实看出了直播教学的好处。王学语记得,当时的冕宁中学从高一新生中选出两个尖子班,一个直播班,一个对比班,生源水平持平。一两届后,直播班的尖子生们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形成碾压性的优势。
王学语说,2007级直播班,学生几乎占满了年级前十名,高考时还出了西昌市第七、八、十五名。而另外的对比班,没人进入西昌市的前二十。
那一年,冕宁中学有几个学生考入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四川大学等名校,但他们入学时的中考成绩并不拔尖,西昌的中学,甚至没打电话来“挖”过。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学校对直播班有了很大的信心,质疑的声音消减下去。
2008年,同在大凉山深处的盐源中学也开始了直播教学。副校长林新明说,初衷同样是稳定生源。
如今已在浙江大学读大二的王立,于2014年进入盐源中学直播班,那时她的中考成绩,在县里排到六七名。
进入直播班后,王立和同学们不仅要上成都七中的课,还要用成都七中的习题和考卷。第一次考试,16岁的王立就感受到了与直播屏幕另一端的差距——数学16分,“我考了和我年龄一样的分数”。此外,王立的其他理科成绩也只有三四十分。
高一时,他们开始做高三的英语阅读题。每次做题,王立要翻着词典把所有单词查一遍,一对答案,选择题还是全错。
屏幕两端的老师同样存在差距。冕宁中学2013级直播班毕业生王绡(化名),如今在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念研究生。中学时,她最喜欢成都七中的一名数学老师,那是一位清华大学数学系硕士。他在课上提到的一些前沿理论,王绡在冕宁中学的老师都没听说过。
王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那位男神数学老师在画图时,“非常自然地”写下了很多数学概念的英文单词。“屏幕那头七中的学生‘哇’的一声,我们这边也非常惊喜,跟着‘哇’,觉得太厉害了!”
更大的差距来自对高考动向的把握。我读高中时,还是四川省高考自主命题的时代,有任课老师从成都回到凉山,说一些高考不再考的内容,他们都不知道,还在让学生一遍一遍地练习,可“外面的老师”都知道。
西昌市一名考上北大的学生说,高三时,她做过成都七中的模拟题。与凉山州的高考模拟试卷相比,那份试题“更接近高考风格”。

2月1日,四川省冕宁中学的一面墙上,展示直播班学生的英文书法比赛。新京报记者付子洋 摄
从扩张到“下网”
盐源中学的第一届直播班,就出了几个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名校的学生,23人上了一本。而之前的很多年,这个数字都只有10个左右。到了2014年,得益于针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高考三大专项计划”,盐源中学的一本上线人数升到了38人;2018年升到了78人。
副校长林新明说,有一年春节,那个考上北师大的学生到西昌探亲,告诉亲友自己是盐源中学毕业的,别人听了直摇头,“说不可能,盐源中学怎么出得了北师大的学生?”
由于直播班的成绩好,越来越多的孩子想要挤进去,凉山各地的高中直播班也越来越多。比如在盐源中学,高一新生的前200名都有机会进入直播班,但林新明说,真正能够适应直播教学的大概只有前60名。
在王学语看来,成都七中教学容量大,特别重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那些基础好、能力强的学生,在直播教学中受益匪浅;反之,则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高一刚开学时,许多学生觉得看直播屏幕上课很新奇,“像看电影一样”。但这些“电影”没有美丽精致的画面、引人入胜的情节,枯燥得让人昏昏欲睡。尤其到了夏天,教室里拉着窗帘,光线黯淡,空气闷热,没多久学生们便倒成一片。老师时常要拿着教鞭在教室里巡视,遇见打瞌睡的学生便提醒一下。
下课后,直播班的孩子也要付出更多努力。王立说,上高中后,她每天都要把当天遇到的数学题研究透彻、把英文单词查清,再预习好明天的功课。高中三年,她每天都在凌晨后才睡。

直播班的学生正在上课。受访者供图
重压之下,学生们的情绪很容易波动。王学语说,高一时的班会课常会变成诉苦大会,“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哭过”。还有一名学生压力太大要退班,王学语特意打通了成都七中老师的电话,请他帮忙鼓励学生。
冕宁中学的老师梁青成(化名)带过一个直播班,高三毕业时“蒸发”了20人。除了分科时转去文科的几人,剩下的人都因为无法适应网班教学,中途退出。
直播班的老师们也要适应新的教学方式。用王学语的话说,远程直播教学就像一条学习的高速路,学生是乘客,远端老师才是驾驶员。
比如,有的老师会让学生一边听课一边记笔记,下课后把笔记本收上去一一检查,英语连草稿纸都要收;有的老师会将直播改成录播,遇到重点或学生听不懂时就及时暂停,深入讲解。
近几年来,凉山州各中学的直播班中已有不少关闭了直播屏幕,只用成都七中的资料做题。
一位今年带高三直播班的老师说,一次模拟考试后,学生们的物理成绩一塌糊涂,全班62人中40人要求“下网”。学生说,“老师,你还不下网哈,再跟直播就跟‘死’了。”
“我想考600分,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
设立直播班的初衷是稳定生源,但很多老师也受到了影响。林新明介绍,2008年开办直播班时,盐源中学刚引进一批本科毕业的年轻老师。有的老师每天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地研究七中的教学方式,现在他们已成为学校的中流砥柱。
不过,基层中学依旧很难阻挡超级中学的“虹吸作用”。在所有学校中,成都七中这样的超级中学无疑站在了金字塔尖。
前几年,一名县城中学直播班的老师负责应届生招生。听说附近乡镇的学校里有个学生“很有灵气”,校长都亲自开车去学生家里游说。这位老师说,那个学生瘦瘦小小的,“像个还在滚铁环的娃娃”。这个娃娃最终去了州府西昌的一所重点中学,并在高考时成了全校的理科状元。
身为一名父亲,梁青成认为可以理解生源流失的现象。“如果是我的娃娃,能读成都七中,那绝对不读西昌一中。能读西昌一中,那肯定不读普通高中。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直播班通过那块屏幕、那些习题,让留下来的学生可以触摸到省会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
除了直播课程,近年来,教育部针对全国农村和贫困地区的“高考三大专项计划”,也让更多寒门学子有了就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据澎湃新闻报道,2018年该计划共录取学生10.38万人。盐源中学一位直播班毕业生告诉我,他能最终考上名校,便是得益于“国家专项计划”。
2月2日下午,因为我的采访,盐源中学2014级的4名毕业生回到了从前的教室。教室后面的一面“心愿墙”上,学生们用五颜六色的贴纸,书写着自己的朴素愿望。他们有的想当外科医生,有的想去北京,有的想要考上理想的大学。

2月2日,四川省盐源中学一间直播班教室后面的“心愿墙”。新京报记者付子洋 摄
一名学生看着这些贴纸喃喃自语:“从前我在这里写着,我想考600分,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
不眠不休的城市停下脚步,在岁末,把想念打包进行李,一张车票,送游子回到故乡。
母亲煮好的饺子代替了打卡和签到,父亲递来的茶代替了交际和应酬。小火慢炖的汤,咕嘟咕嘟熬,辞旧迎新的爆竹响起,旧符换成新桃。
钟声里,亲人围坐在年夜饭旁,一手攥着2018的收获,一手攥着2019的热望,每一张年轻的衰老的欢喜的沧桑的脸,都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用小人物的视角,打量着大时代的脉络。
或许是城市建设者,或许是异乡羁旅客,或许是老翁不离故土,抑或许是年轻人四处漂泊。新春的焰火把他们会聚到一起。
沿袭历年的传统,我们继续记录故乡。用一年一年的回望,讲述正在发生的改变;用每个人的三言两语,勾勒出“故乡里的中国”。
原标题:大凉山里的“一块屏幕”:县城中学逆境突围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