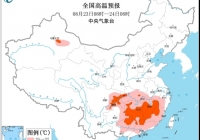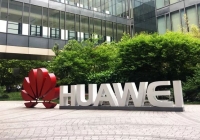他觉得纪实摄影是需要勇气的,也无奈现在车厢里人情寡淡了不少,“现在全低头看手机。”

最近,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一批来自中国的老照片站上了C位。
黑白影像里,中国旅客在火车的方寸间,休憩或交谈,蜷缩或者舒展,没有宏大叙事,全是日常生活的诗意。

有张拍摄于1994年的照片引起了讨论,一位中年烫头男士,穿西装打领带,右手夹着一根香烟,左手戴着机械表拿着大哥大,正专注地听电话。照片流传到社交网络,有懂行情的网友惊叹,“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土豪中的土豪,当时一部大哥大的价格起码相当于iPhone X的十倍乃至十几倍。”

西装、手表、大哥大,90年代土豪的三件套。注意,那时西装的商标要外露,绣在袖子上,让人看见牌子。
这些照片出自摄影师王福春之手,人情冷暖,善恶美丑,都在胶片里,构成了年代纹理的一部分。为了拍摄,他曾被车长“监视”,被小偷当做同行,被乘客误会暴打,却没有想过停下来,从绿皮火车拍到“和谐号”,王福春对火车摄影几近痴迷。
王福春在2001年卖了三台相机,自费出版作品集《火车上的中国人》,印刷2000册。每张作品像一个线索,解开了当年人们生活与情绪的细节,如今在淘宝炒到近500元一本。

摄影集先后再版五次,2017年版的豆瓣页面上,热度最高的评论写道,“想起上学时经常乘坐昆明到攀枝花6162次慢车的场景,翻一本书,随身听、几节电池、几盘磁带,一路停,一路走,昏昏欲睡,被风吹醒,沿途一幕幕静谧的村庄,河流,山脉,城镇,烟雾,霭岚,穿过无尽黑暗潮湿的隧道,闪过无数陌生鲜活的面孔。”
那时候的火车慢,生活也慢,没有“低头族”。上了长途火车,以家庭为单位的人们进入临时的集体生活,变着法儿消磨时间,到处都是景。
在火车上摄影,“像小偷”
长年在火车上活动,王福春练就了一双“贼眼”,时而飘忽,时而机敏,“跟小偷一样,经常和小偷不期而遇。我看他像小偷,他看我像小偷。”他笑称自己何尝不是“职业小偷”,“我偷的不是旅客财物,是旅客影像。”
怎么个“偷”法?
每次上火车,他会从第一节车厢走到最后一节车厢,看看有什么特殊乘客。那时候火车晃动得厉害,采光也不好,他要像一只猎豹,守着“猎物”,伺机出动。纪实摄影需要手快,他琢磨出了要义,“原地35毫米,前进一步50毫米,后退一步28毫米,用腿丈量改变焦距。”

火车上鱼龙混杂,王福春来回走动,容易引起注意,再带个相机,更让人防备。乘务员质问他做什么,他亮出铁路摄影师的工作证,以为能从此一路绿灯。谁想到没一会儿车长来了,客气地把他安排到卧铺休息、到餐车喝茶。他起身走到哪儿,车长就跟在哪儿,根本没法拍摄。
他见招拆招,穿件马甲作掩护,把相机斜挎在马甲下面,直到等来“决定性瞬间”,才抽出相机迅速按几下,再将相机藏起来。
一串动作几秒钟就能完成,他力求成为人群中的“隐形人”。“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拍摄,把相机隐蔽掉,镜头对着你,但是我的眼睛却看着别的方向。”王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传授抓拍技巧。

融入人群也是一种拍摄手段,走在东三省的线路上,就说东北话,走在川渝线路上,就说四川话,走在江沪线路上,就说上海话。从1978年开始拍摄到现在,东至上海,南至广州,西至格尔木,北至漠河,他几乎把中国跑遍。
“但在每个城市都没那心思玩,都在车里头。”这是个以火车为家的人,往往一趟火车拍得差不多了,马上就近下车,到月台找其他车次拍摄。
对火车的“痴”,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王福春从小住在火车站边上,晚上听着火车轰鸣声入睡、白天到铁道边捡炉灰渣子,在心中种下了火车情结。
初中毕业,他考上哈尔滨铁路局司机学校,从检车工干到宣传干事。一次偶然机会,王福春收到上级任务,拍摄技术大练兵。这位中国铁路摄影第一人,第一次正式拿起了相机,开启他长达四十多年不知疲倦的“疯狂拍摄”。

1984年,为了专心摄影,他申请调到铁路系统的摄影师岗位,专门拍摄火车上的见闻,发布在地方铁道报上。“我成天往外跑,那时候有工作证免票,疯狂地拍。最多一年坐火车拍了一百三十多次。”他一度只能在火车上睡好觉,回家就失眠。
坐一次火车拍数百张,能选出一张经典就算“很了不得了”。拍到痴迷,顾不上吃喝,他曾在一个夏天虚脱昏倒在车厢,也曾因为来不及上车,从月台跳上行进的火车,差点掉进铁轨丢了性命。
“你不疯狂,你不傻,你成不了气候。”在一次线下摄影沙龙上,作为主讲人的王福春和年轻摄影爱好者分享道。
“越是绿皮车,越出故事”
上个世纪80年代,飞机线路少,价格高,火车是普通家庭出行首选,赶上“民工潮”,火车上常常人满为患。“那时候不按座号坐,上车的时候大家都想争座位,这儿拿帽子占一个,那儿拿双鞋占一个。”王福春回忆。1985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为52119公里,不到现在铁路营业里程的二分之一。

绿皮火车速度慢,设备简陋,夏天靠开窗通风降温,冬天靠锅炉烧煤供暖,却是王福春的宝地,“越是绿皮车,越出故事。人多得很,什么故事都有。”

上个世纪,列车员是令人艳羡的工作。列车员常年跑车,在物流不发达的年代,能接触到各地商品,做点“代购”生意,“那时候有的列车员从广州那边带烟,烟都是成箱的买,运到哈尔滨后卖。”
没有移动支付的时代,人们出门习惯带现金,犯罪团伙抓住这点,一度非常猖狂。火车开到后半夜,小偷团伙上来了,在熟睡的乘客左右两边各站一人,拿着刀,上去掏兜,到手以后就下车。

王福春那时候为了防盗,故意“背个破包”,随身带着,也有的旅客带着体面的皮包,为了防盗,用铁链锁把箱包锁在行李架上。

改革开放初期,个性与潮流突然行上快车道,年轻的男女开始在衣着上寻特色、赶时髦,“80年代初流行的是解放服,80年代末流行喇叭裤蛤蟆镜,91年开始流行文化衫,93开始流行西装。”76岁的王福春自有一套流行演变图谱。

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是稀罕的物什,铁路为了创造营收,推出放像车厢,列车员会举着广告牌子吆喝,“第十号车厢是放像车厢,演大片,谁去?有座。”80年代后半期,有些车次开始在全车安装电视。

火车上缺热水,往往行程没到一半,热水就没有了。这为沿途的小商贩提供了商机,列车停靠时,卖热水的商贩拥过来,乘客从车窗把水壶递出去,论壶卖。

1999年,王福春上了一趟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火车,那时候铁路刚经历第二次大提速,全国旅客列车平均时速达到近56公里,但到乌鲁木齐也要三天。途中,列车员发动大家做广播体操,“在广播里说,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一听我赶紧跑过去拍。”翻动他的作品集时,王福春余光一瞥,就能说出照片的拍摄年份、车次和由来。

高铁拍片被暴打
“摄影就是上贼船的感觉,上去下不来了,你走这条道以后,你不能停。我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今天,那是一个完整版改革,就像火车车厢一个扣一个,中间就断了就不是火车了。”在王福春看来,人的一生,做一件事就够,坚持做半个世纪,能成大家。
他想继续拍下去,但是并不顺利,甚至吃过拳头。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注重隐私,对于陌生人的镜头有抵触情绪。2015年,72岁的王福春坐火车到杭州讲课,在火车上抓拍了一个妇女和她的孩子。“结果她爱人就坐在旁边看见了,他就尾随我,把我当坏人。”走到车厢连接处,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一把掐住他的脖子,一拳打到嘴边,出血了,牙也松了。
王福春找车长报警,说明情况,小伙子一直道歉,“我一看我嘴破了,牙也活动了,但我还能说话,我一看原谅他了,算了。那次是暴打,过去在车里怼你两拳,踹你两脚是正常的。”他觉得纪实摄影是需要勇气的,也无奈现在车厢里人情寡淡了不少,“现在全低头看手机。”

从前,绿皮火车的座位是面对面安排的,一排一个长凳,人坐下来免不了寒暄几句,“有酒同喝,有烟同抽”。王福春曾在北京到沈阳的火车上看到旅客支起了好几桌麻将,一问才知道,原来列车为增加收入,开辟了麻将出租业务。

除了麻将,还能租小电视,三四个人围在一起看大片,还有下棋的,玩乐器的,逗宠物的,玩插卡式游戏机的……坐一次火车,认识一帮朋友。如今,老照片连带着老时光的人情味在社交媒体上又鲜活起来,掀起一阵怀旧的叹息。

一边怀旧,一边与时俱进。2002年,王福春来到北京生活,开始拍摄地铁系列照片,“地铁是火车的姊妹篇,就觉得这个题材是我的,我应该拍。”地铁光线差,胶片机出片成功率低,加上胶片越来越贵,他逐渐改用数码相机拍摄。

他每天把半个手掌大小的卡片机别在腰带上,有时候出门忘带了,不管走了多远,都要回家取。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这天,王福春和记者在车上看到一起车祸,路边一辆白色轿车冲倒了栏杆,翻了个底朝天。王福春立马翻出卡片机,连续按下快门。
接下来的十分钟,说话间他多次翻看刚才拍摄的照片,喃喃着“如果刚才在你那个位置上能拍到更好”。
原标题:抽烟喝酒烫头,80年代坐绿皮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