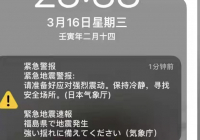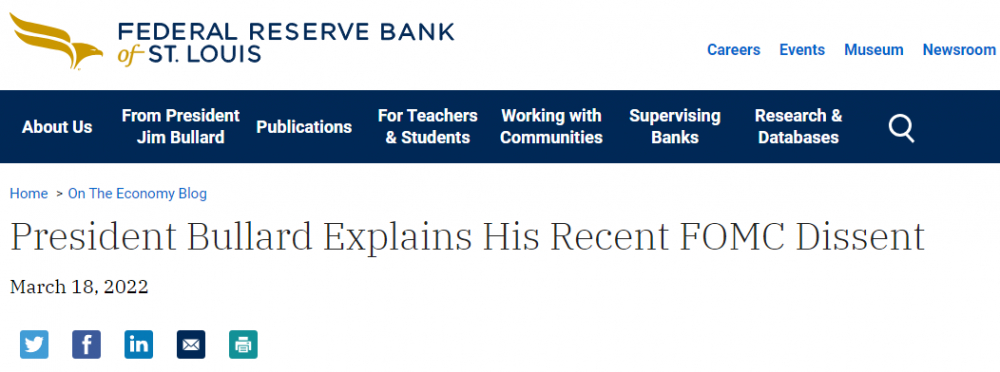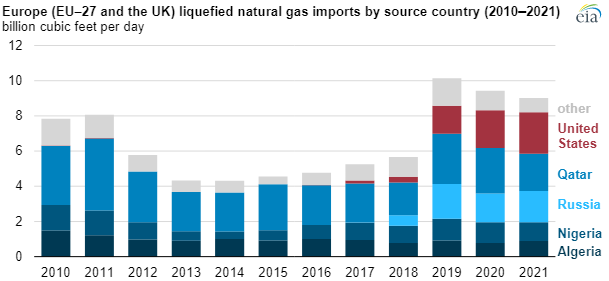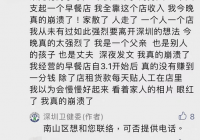冰点周刊消息,0时,北京市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24小时健身房,和白天一样明亮。
熊敏在一台跑步机上运动——它位于最角落,右侧紧贴墙壁,离所有健身器材最远,站在上面的人拥有某种“不被注意”的安全感。这是深夜健身带给她的“特殊权利”——如果提前两个小时,跑步机上永远有人,像一场接力。
据保安观察,深夜健身者大多数会在22时到23时30分之间进门,最迟次日3时还没离开。来者大多是年轻人,男性占多数;每天都有新面孔,鲜有人夜夜坚持;夜深人静,跑步机最受青睐,杠铃、器械则不那么受宠。
一位24小时健身房老板,将深夜来健身的人归纳为几类:附近餐馆的服务生、办公室里加班的“社畜”、失眠者,以及被老婆赶出家门的中年人。
1
夜深了,健身房里几乎听不见交谈,白天火热的音乐、金属器械撞击的声音也安静下来,只有头顶的空调发出低低的轰鸣声。
熊敏穿着一身黑色运动装,戴鸭舌帽,手机里放着电视剧,在跑步机上快走着。她喜欢安静的环境,便于运动时思考,再加上长久以来的失眠,她将健身的时间固定在每天22时30分以后。
曾有一段时间,熊敏总是凌晨一两点时来到健身房跑步,配速稍稍提升,她会感到心跳不正常地加快,心脏一阵刺痛。“字节跳动员工在健身房猝死”“北京一男子在健身房内猝死,家属索赔166万”“34岁重庆男子健身房运动后猝死”……“健身房猝死”的新闻让她担忧。
她对照新闻里的描述一条条检查自己属不属于类似的“高风险人群”,最终她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一个普通互联网‘社畜’,不常有‘劳动密集型加班’,精神压力没那么大。”于是第二天,结束加班后,她还是转头走进了健身房。
1时,熊敏走下跑步机,往家里走去。她会在2时左右准时入睡,在3时和凌晨5时分别醒来——由于失眠,她每天的深度睡眠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
短暂的睡眠过后,是早高峰与漫长的通勤。之后熊敏坐进公司格子间,与电脑屏幕、会议、外卖度过一整天。她在一家互联网医美公司负责App的页面运营,虽然工作压力比不上“大厂”,但忙的时候也要加班到22时多。熊敏不到30岁,肠胃和腰椎都出了毛病。
2020年初,熊敏的前公司精简人员,修改了绩效考核制度,按照加班时长确定每个人的绩效,并要求周日加班,一些员工“被迫”辞职。离职浪潮中,熊敏遭到同事的孤立,部门的团建,她是从同事忘了屏蔽她的朋友圈中知道的。
强撑了两个多月,熊敏提出离职。她原本等着公司裁员,拿一笔补偿款,这下补偿也没了。那一段时间,熊敏常在深夜痛哭,也会一口气吃掉7个甜甜圈,体重暴涨了20斤。辞职过后,熊敏回了大连的老家,休养生息。
幸好还有跑步。挣扎在无止境的加班、同事的“冷暴力”,以及不知道何时会到来的裁员中,“跑步”是熊敏唯一能够抓住的一点“确定性”。相比起工作,跑步的回报是明确的,多跑一公里,就多收获一公里的乐趣。这是她坚持了4年跑步的原因。
最开始的时候,她只能跑3公里,渐渐地,5公里、8公里、15公里、20公里……跑步机上的数字不断刷新,熊敏感到一种巨大的快乐,她开始相信,“只要你去做了,肯定就会变好。”
2020年8月,熊敏回到北京,找了一份新工作,“老家挺好的,适合‘躺平’,感觉那里的人,脸上都没什么欲望。后来想,如果人生真的还想有什么进步的话,还是要去大城市。”回到大城市后,熊敏在新公司附近的健身房里办了一张卡,深夜继续在传送带上秘密前进。
2
熊敏加入的这家连锁健身房,是国内“24小时健身房”的代表之一。创立不到5年,它的全国门店数量达到了近800家,其中北京有141家,朝阳区最为密集,有59家——平均每8平方公里就分布着一家。 根据全国门店统计,有十分之一的客流是在22时至次日8时走进健身房的。
相比传统健身房动辄上千平方米的面积,这类24小时营业的健身房往往只有300平方米,设施少、成本低,像“便利店”一般密集开设,且采取月付制,健身的门槛降低了;健身房的门禁通过特定App扫码进入,因此即便半夜店里无人看守,健身者也可以自由出入;跑步机同样依靠扫码运行,每一次跑步的数据都会被录入系统,成为健身者运动过的证据。甚至,在互联网的管理逻辑之下,健身教练在这里也拥有更多的自由。
教练郭驰可以选择“不驻店”,只在有课时来到健身房。但也因为“不驻店”,郭驰丧失了在App上被推荐的机会,只能依靠老客户推荐新学员。在App的界面上,每一位教练的累计课时、证书、好评率、以及过往学员的评价都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决定着推荐位的排序。在这类健身房中,教练没有底薪,代课量决定其全部收入。
“互联网”模式的健身房有着一套极其详尽的规则,一旦监控摄像头拍到教练违规——比如教课时坐下了,便会对教练进行处罚。有时,总店的客服——那些监控后面的监督者,会到店面对教练进行检查评估。
教练蒋希原本是一名培训机构的老师,也是一名资深的健身爱好者。或许是因为练得久,从去年开始,她频繁地被一同上团操课的学员夸奖“可以去做教练了”,又被代课的教练怂恿,决定去考一个舞蹈教练证。一个月后,她通过考核,成为了一名兼职健身教练,同时在3家健身房代课。
正式进入这个行业后,蒋希发现,团操对于女教练的身材要求比男教练更加严格。虽然没有哪家健身房明文规定女团操教练一定要瘦,但蒋希常常能在下课之后听到学员聊天,“我希望那个教练更瘦一些”,或是直接在课程的评论区评价教练身材。
蒋希很快接受了这份职业的要求,并开始控制饮食,而她的体重只有100斤出头。“这个舞蹈本身叫什么?叫燃脂舞,就是为了变瘦才来跳的,你越跳越胖,谁还跟你跳?”蒋希说。除了身材以外,对女团操教练的要求还包括长相,以及“有没有化妆”。
当上兼职健身教练没多久,蒋希工作的培训机构倒闭了。她在失业的痛苦中暴饮暴食,开始疯狂摄入减脂期不敢碰的主食——米饭、馒头、面条、饼,以及大量的酒、炸鸡、巧克力派。
今年1月,蒋希终于找到了一份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朋友们看到她,惊讶“怎么变得这么胖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蒋希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强迫自己断掉暴食。每周6天,她下班后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待在健身房,直到深夜。
3月7日这天,蒋希离开健身房的时间比平常更晚一些。她等到团操教室空下来,将手机架在教室中央,举起地上的杠铃,开始录制自己的杠铃操教练考核视频。
空旷的教室里,随着每一次杠铃推举,蒋希背部的肌肉有规律地起伏着。这个女孩不满足于有氧训练带来的纤细身材,她更向往拥有一身“大肌肉”,她的新目标是考一个杠铃操教练证。22时,她开始了加练。

深夜健身房里“撸铁”的人。视觉中国供图。
3
22时,也是餐厅打工者潘晨骏到达健身房的时间。餐厅21时30分关门,收拾完后厨,潘晨骏骑上共享单车,直奔健身房。他总是先在跑步机上跑40分钟,再练一遍所有上身器械,一套练下来,大约两个小时。
一年前,20岁的潘晨骏从老家山西来到北京三里屯的一家餐馆打工,过着“睁眼、上班、下班、合眼”的生活。那时他的体重是220斤,看着镜子里臃肿的身体,他在心里反复安慰自己:“挺帅的,也不胖嘛。”直到餐厅里相熟的阿姨连着好几天在他耳边唠叨,“小潘啊,你瘦下来一定更帅气。”潘晨骏感到没法再自我暗示下去了,便挑了一个下班早的日子,去24小时健身房办了卡。
刚来到北京的时候,他过得并不开心。后厨的工作繁杂,一站便是十来个小时,油烟呛人,一早上下来,口罩被熏得发黄。一天中最忙的时候,潘晨骏形容“就像在做一个梦”,脑子里一片空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菜就那样做出来了,一道接一道。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机器,一年四季都被困在一方狭小的空间里,重复着同一套动作,从早到晚。
直到健身之后,枯燥的生活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追求,或是一种“变好”的强烈冲动——曾经连续一个月,潘晨骏在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里也要跑来健身房,一天练两次,练到最后,端锅的手止不住地抖。
2021年春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潘晨骏留在了北京,头一次有了充足的时间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转一转。“以前你不明白的那些东西,到这儿一看,一接触,就会发现,原来世界真的很大。”这个年轻的男孩忽然严肃起来,好像在宣告一个重大的决心——“所以我要来健身,因为我知道在大城市里,只有改变了自己,你才有机会接触更多你从未接触过的东西。”
“深夜健身”似乎在大城市更流行。压力、繁忙、更多的竞争者、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对于外表更高的要求,都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深夜走进健身房的理由。
在运动医学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来证明人在哪个时段运动是比较恰当的。但在一则采访中,上海体育学院运动防护教学团队成员侯希贺提出,从医学角度来说,有质量的睡眠在改善整体健康及提高健身效果方面尤其重要。有研究显示,23时至次日1时,人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睡眠效果更好,因此,他并不建议在这段时间内锻炼。
但对于深夜健身者而言,睡眠要让位于更重要的东西。一位女性学员总是在22时来上私教课,她工作繁忙,经常出差,家中还有身体不好的丈夫和孩子要照料。但一踏入健身房,她依然精神抖擞。23时下课后,她还要在跑步机上跑半个小时。“为了减肥,她好像什么都能做到。”她的教练说。
(应受访者要求,郭驰、蒋希、熊敏为化名)
原标题:深夜健身房藏着1000种秘密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