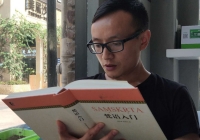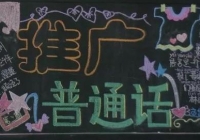冯仑
30岁以前,冯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和改革扯上直接关系。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突然社会上多了个词‘改革’。起初并不知道这个词将与我个人生活发生多大的关系,无论是本科、硕士毕业,还是开始工作,似乎关于这件事情,我都是在关注别人的所作所为,对别人做得不对的事情希望有改变,或者想把事情往更好里做。”
冯仑在最近的一段回忆中描述,改革之初,他懵懵懂懂地参与到了“改革的吃瓜群众”行列,完全是从一个看客的角度去窥探、去加油、去使劲。
那段“改革吃瓜群众”的岁月,是轻松愉悦的。“上世纪80年代的状态,特别兴奋,因为当时思想空前活跃。”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0岁以前,跟时代最大的连接,除了上班,就是大量参加社会活动,“只要有跟改革有关,跟新思潮、启蒙这样一些理论研讨有关的,都特别积极去参与”。
彼时,冯仑在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工作。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像前辈一样,沿着“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路径走下去,这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普遍路径。
但没多久,冯仑离开了体制,成为自由人。他形容自己,“从车上被颠下来了”。而到了体制外,他才发现,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每一次改革都跟自己有直接关系。
“被改革”的前半生
1977年,冯仑18岁。
这一年,正是改革开放前夜,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安排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废除推荐制,恢复了高考制度。在此之前,高考这扇大门已经关闭了整整11年。
冯仑高中毕业,恰好赶上恢复高考。冯仑看完母亲用蜡版给他复印的资料后,借来一辆自行车奔赴考场。“当时考场的课桌都是破破烂烂的,桌面高低不平,有时一写字就能把考卷戳出一个洞。”
冯仑考上了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这是新设立的专业,首批招收了50人,冯仑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同班同学中,有的是知青,有的已经三四十岁有了孩子,而冯仑是大学里最年轻的学生之一。
本科毕业后,冯仑又考上了中央党校的法学硕士。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他通过大量阅读,建立对外界的认知,尤其是对真实世界的了解。
他后来在自己出版的《野蛮生长》一书中回忆:“中央党校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就是内部资料(内参)阅览室。当时是按级别看内参,很多资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资料反映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我突然感觉,原来除了我们从《人民日报》看到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外,还有这么多真实的情况!我开始怀疑,渐渐形成了习惯,在内刊室里找史料,不停地看各种各样的内参,这些资料使我知道世界原来是由两面互补的,一面是宣传,另一面是内参。”
年轻的冯仑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思考的都是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大问题”。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也和主流保持一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胡乔木那样著名的“笔杆子”。“那时候最高理想就是成为胡乔木这样,天天写字,然后给领导写点文章。”
毕业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去了中宣部、体改委。
29岁那年,冯仑第一次来到了海南,着手创办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会从海南开始,转了一个大弯。
1988年,海南正式建省,成为最年轻的省和最大经济特区。由于国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海南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和憧憬的热土。
不过,冯仑在海南的第一次冒险没有成功。当时,海南省体改所既没有财政拨款,也没有启动经费,随后被撤销。他回到北京,遍托关系找工作,但所有国家机关都对他关上大门,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
“颠下来后才发现,自己被改革了,于是只好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向。”冯仑回忆。
但是重新寻找方向并不容易。这其中值得回忆的一段人生插曲是,回到北京后,冯仑误打误撞来到了南德公司,成为“狂人”牟其中的副手。牟其中的做事风格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曾以500车皮轻工产品,换回前苏联4架民航机。牟甚至扬言:要在喜马拉雅山炸一缺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中国,把落后的西部变成第二江南。
书生气的冯仑和江湖气的牟其中注定无法成为同路人。1991年,冯仑不辞而别,正式闯荡海南。
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后来又有潘石屹加入。日后,他们被称为“万通六君子”,他们的聚散和沉浮,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注脚。
为什么选择海南?其实并非偶然。冯仑说,因为要自谋生路之后,总会选择“激情四射和认为有机会的地方”。
“在被改革的状态中找到了海南大特区这个热闹非凡的改革热土,于是我们开始在那里野蛮生长。”冯仑说,“六兄弟”一致认为海南是“最容易生长的地方,最容易绽放和最轻松的地方,也是最不怕失败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着最多跟我们一起尝试在失败中找到方向的人”。
“万通六君子”的海南往事,已经被无数媒体挖掘、加工和呈现,关键词几乎都是“冒险”。
建省之初,中央政府给予了新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资金和淘金客一起疯狂地奔向海南。
万通赚到第一桶金的故事,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现在听上去非常疯狂,但在当时的海南却十分盛行。
1991年,六兄弟在只有3万元起步资金的情况下,冯仑找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和对方谈合作,“有一单项目,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对方同意后,500万一拿到手,冯仑马上跑出去写文件,王功权骑着自行车迅速拿到钱,然后从银行贷出了1300万,再以1800万作为本金购入8栋别墅,然后出手,赚取了300万利润。
“早期很多民营企业管理就四句话: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贷款为收入,以笼络为管理。”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期海南的民营企业很多就是这样的生存方式,但这些方法论对于以后做企业,“都是致命的威胁。”
冯仑还曾对媒体讲过一个细节,“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然后强迫签下一个合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人身上。”
自由而疯狂,这是当时整个海南的气息。不仅冯仑,六君子的每一个人,都迅速完成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身份转换,并且享受这种自由和狂热。
“至今想起来,在海南那样一种自由的热土,无拘无束的表达,快乐的行走,艰难的忍耐,都变成了美好的经历。”回忆往事,冯仑依然感慨,因为当时什么都没有,就意味着什么都不会失去,也就意味着得到任何收获都会开心,“在海南真有一点儿童般的快乐”。
“心里有未来,脚下才有道路”
1992年底,“六君子”的海南农高投注册资金已经改写为5000万元,当年的“皮包公司”已经实现了华丽转身。
在商业规则一片混沌的海南淘金潮中,他们活了下来,并且初尝了成功的味道。不过,这个时候,对这6位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年轻人来说,赚钱仍然不是他们的信仰,他们试图寻找到比赚钱更有意义的目标。
“到 1992 年,公司创办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就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们几个一起创业,而不是别人。这成为我们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结合成一个特殊的企业群体?我们该如何讲述自己?”冯仑回忆,六个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副标题是《知识分子的报国道路》。
六个人,都曾有“书生报国”的志向。冯仑毕业于中央党校;王功权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易小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专业;王启富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又去了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刘军16岁就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只有潘石屹学历稍逊,最初只考上了中专,后来继续报考了大专。
不过,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洪流中,“六君子”都脱离了主流路径,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尽管身份已经下海,但在内心,他们更愿意向知识分子靠拢。
“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一起创业,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信仰,为了国家的未来。”冯仑说,现在看来这个话题有点宏大,但就像当时王功权说的几句话,做这件事对得起自己、养得活自己、对得起父母。也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员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做的具体的阐释。”
怀揣着信仰,“六君子”选择了梁山好汉式的内部管理方式:座有序,利无别。在工作上有分工,在利益上平均分配。
1992年,冯仑和潘石屹嗅到了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气息,将资产抽离海南,转战北京,躲过了即将崩盘的海南楼市泡沫。1993年,万通在北京成立。1995年,万通的触角已伸进房地产、通信、服装、商业、信息咨询、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领域,地盘扩及北京、海南、西安、沈阳、武汉。
就在万通总资产达到70亿元时,“万通六君子”最终还是因为理念的巨大分歧,最终散伙,各立门户。
潘石屹带着他的“SOHO”系列离开万通;王功权远赴美国转行做风投,创办“鼎晖创投”;易小迪成立了阳光100集团,继续做房地产;王启富成为“海帝地板”总裁;刘军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只有冯仑一直留在万通集团。
这次分道扬镳,在感情上是痛苦的,但对未来,也可能是最合适的安排。
“这就像两个不成熟的小孩,结婚过日子又生孩子,早晚是要散的。”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以用婚姻来理解6个人的聚和散,结婚是误会,离婚才是理解,精神上的婚姻永远比身体和现实中家庭的婚姻要更久远。冯仑说,他们6个人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婚姻,“我们的价值观是相近的,所以一直都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留守万通的冯仑,带领万通在地产界拼杀,直到2011年,冯仑宣布卸任万通地产董事长的职务,并逐渐淡出万通实际控制人的角色。
万通地产在地产界的体量一直不算很大。2003年底,万通地产资本金和年度营业收入已双双进入中国房地产企业十强。但十年之后,万通依旧在二线房企行列徘徊,而万达、万科已领先成为行业龙头。
冯仑放弃了万科、保利得以称王的“大规模拿地开发”的快周转模式,而走“轻资产”路线,在地产圈跑马圈地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其他同行。
对于错失过的机会,冯仑曾经有过反思:“2002年后,万通刚刚还完债,我们不想高负债,用高杠杆来撬动市场,结果万通失去了一段发展的好时期。”
不过,万通在业内,更多是以房地产行业创新者和开拓者的姿态著称。而冯仑,因为对房地产模式的不断思考和折腾,收获了“地产界思想家”的称号。
他在国内首倡房地产的“美国模式”(即由全能开发商转化为以投资能力见长的专业的地产投资公司)。他还曾一度痴迷于自己的地产“理想国方案”。2009年底,他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世,也即后来的“立体城市”计划。按照其描述,立体城市将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造起500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集群,运营商试图通过发展产业、提供医疗、社区服务等为数十万乃至百万人口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这是一个据称要花费5~7年、斥资500亿元打造的理想国,但这样一个需要持续的、大规模资金投入的计划显然会影响万通地产的业绩。于是,冯仑选择在上市公司之外进行自己的试验,但最终却遭遇种种困难,进展一波三折。
事实上,冯仑一直不满足于做一个传统的开发商。他一直在不断反思房地产领域的根本问题,反思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他思考最多的是房地产的调控模式。
“我觉得改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摆脱一个传统的观念和做法,就是把市场当下级,用文件和会议管市场,而不是用法律。”冯仑说,今年 1 月份到 5 月份,各地区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文件已经累计出台了 200 多个。从目前的势头来看,文件下发的速度和趋势还在加快。用文件管市场的结果,就是企业的预期难以管理,面临的制度成本正在逐渐提高。“这种方法如果不改变,靠发文件来管市场,靠会议来管市场,靠批示讲话来管市场,只能加大市场化改革的阻力。”
“我最早在机关工作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本,里面记录了每一个人的生理周期和使用计划生育工具的次数。我才知道那个年月,生孩子的机会都是组织上配给的。如果经济到了这种程度,就是最糟糕的经商环境。”冯仑非常忧心,制度成本让现有的创业者在做长期决策的时候时常陷入迷茫,企业家对自己资金周转的速度没办法把控,对于市场的规模更没办法做出判断。“企业家要永远向前看,心里头有未来,脚下才有道路。但如果预期乱了,心里三心二意,脚步就会徘徊,甚至倒退。”
“改革要去的地方 必须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中国地产界,少有人有冯仑这样的学历背景——本科在西北大学读经济,研究生在中央党校钻研马列,2003年又在中国社科院拿到了博士学位。
对于“传道解惑”这件事情,冯仑有很深的情结,先后出版了《野蛮生长》《理想丰满》《岁月凶猛》等书,被集结成了冯仑商业三部曲。
相比他的大部头著作,他张口就来的“段子”影响了更多的人。“好人谈理想、坏人只谈钱”“理想就是把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住房问题是青春痘,扛一段时间就会自然解决”“做公益如大姑娘新婚——幸福又糊涂”。段子太多了,他又把这些精彩的段子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小道理:分寸之间》。
吴晓波说,冯仑是中国企业家的“段子派”掌门,他的商业真相和管理智慧都在段子里。段子太出名了,以至于也给冯仑带来很多困扰。“每当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很多朋友大家都希望,能不能讲个什么段子,我就很窘迫。我又不是郭德纲,我不负责每次都来表演。”
他表达自我的手段,比一般人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企业家像冯仑这样,积极而且热烈地拥抱自媒体。冯仑早在2006年,在万通就创办了《风马牛》电子杂志。2016年紧随新媒体发展趋势,上线了风马牛公众号,做起了脱口秀节目。
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公司团队运营了三个微信公号,加上头条号和微博号,5个号加起来粉丝已经超过了120万。
“冯仑风马牛,在公号里肯定算好的,因为已经赚钱了,有人投广告了。”冯仑说,这和团队的努力,以及自己的勤奋支持分不开。署名冯仑的文章,在公号里出现得很频繁,这些都出自于他的原创。
他创作的方式很独特。“我写法跟别人不一样,我拿手机写,比如说一会到机场了,还有20分钟,我就对着手机说一篇文章,然后发给他们去转化成文字。”冯仑说,虽然有时候让文章看起来有点“口水味”,但这种方式让他很快乐,不需要在电脑前正襟危坐。
在自媒体时代,冯仑的身份是“冯叔”。他乐在其中,甚至开玩笑说,自媒体要慎入,因为他越来越擅长一个人说话。“一个人都能把自己说嗨了,我有时候怀疑自己会不会得神经病。”
2018年2月2日,冯仑又折腾了一件大事,将风马牛一号卫星成功送上太空。除了思想家和段子手,他现在还是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的拥有者。
冯仑希望,能够借助太空技术,打造未来媒体。在他看来,太空媒体,能创造很多独特的内容和体验,比如“太空直播”。风马牛一号这颗卫星就配备了4K高清全景摄像头,可以呈现360度太空高清照片,地面接收者可以看见来自太空的影像,再配合一些VR技术,让用户有亲临太空之感。他希望借此探索一种全新的科技媒体商业路径。
做自媒体,放卫星,在很多人看来,冯仑总是在不务正业。而对冯仑自己而言,他一直渴望打破边界,利用自己擅长的商业方式,去寻求人生更多的可能。
不过,无论折腾多少事,他终归会在商言商。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个阶段,他的主业仍然是赚钱,“有一半的时间是和赚钱有关,30%左右的时间花在公益上,剩下百分之十几的时间给自己。”
“现在我做的事,就三件:赚钱、捐钱、花钱。怎么赚钱,决定怎么花钱,所以做企业一定要有效益。但是赚了钱以后,一定要有所谓企业社会责任,这份责任就包含捐钱、捐时间、捐能力。然后还得为自己、为家人,为了朋友,花钱。”冯仑说,在人生三件事的选择方向上,希望是对个人、企业、社会都有增量的事,“有增量就是不做重复的事情,比如,去湖畔大学做导师,对于民营企业家的训练,这里不同于很多大学的商学院,这就是增量。”
冯仑曾经说过,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他现在依然在身体力行,“朝着一个方向,连续地正向积累,事情就变成了事业。”
回望“被改革”的半生,冯仑说,这30年里做得最多的事情,不是谈论改革,不是自身去体会被改革,而是出差和不间断地飞行。
“我现在一年要飞一百五六十次,所以做生意这半生下来少说也有三四千次的飞行。这种频率的出差,这样的折腾,却总让我感到既兴奋又疲倦,既期待又茫然,既充实又空虚;既感觉到些许成功,又不时有些沮丧;既有过程中的些许快乐,但也有之后的惆怅。” 冯仑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复杂的情绪,实际上主要纠结在这三件事儿上:去哪儿、和谁去、做什么。
“一个国家的改革同样也需要每天考虑去哪儿的问题,和谁去的问题,以及做什么事的问题。” 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八届年会上,冯仑发布了他“给40年的一封信”。他表示,改革的目标一定是消灭改革,改革要去的地方必须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改革的最终结果应该是让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能够感受到道义的存在,权利的存在,市场公平的存在,财产和企业长期发展安全性的存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存在、自我的心灵得到平衡的存在。
冯仑曾说,改革开放40年,他最想写本小说把自己经历过的、看到的、听到的,民营企业发展这40年的震撼、有劲、生动的一些人和事,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书名想好了,就叫《自由塔》,寓意是“选择就是放弃,自由就是枷锁”,就如同他自己“被改革”的三十年。
冯仑今年59岁。从1995年六兄弟散伙,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但“六君子”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聚会。
“每年聚会的时候,大家经常开玩笑互相询问情况,没有一个人坐牢,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转移财产,没有一个人因为经济问题成为‘两院院士’(医院和法院)。”
在冯仑看来,这就证明了一点——“我们当初的这份坚持是真实的。”
回望半生,冯仑很感慨:“在中国社会群众普遍浮躁地去追求金钱和物质的时候,我们这六个人,还有所有一起奋斗的伙伴,都坚守着一个基本的底线,我们形象地称自己为‘夜总会里的处女’,不管别人怎么乱,我们得守规矩。”
原标题:冯仑:伟大是熬出来的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