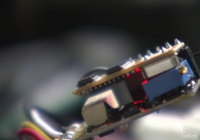澎湃新闻消息,父亲的遗体很快被搬上车,关上后备厢,汽车快速驶离视线,黄健(化名)就这样匆匆与父亲完成了告别。
1月23日10时,武汉“封城”。除了父亲,黄健86岁的舅舅、53岁的表哥分别于2月1日、8日去世。
送走父亲的最后一幕在他脑海中始终无法消散,“就像坐巴士一样,一站接着一站,太没意思了。”
任何一场战役都非单纯的短兵相接,除了疾病带来的伤痛,沉浸在“暴风眼”中的武汉市民,还经历着超越身体层面的创伤。
恐惧疾病、丧亲之痛、失序的混乱,漫长的等待,这些记忆也许将长久藏匿在他们脑中,突然在平静的某一天跳出来,给予狠狠一击。
灾难之后,针对更广泛的民众,将慢性应激影响控制在最小,是一道出给全社会的治理考题。
丧亲之痛
“去年二十六,花市灯如昼。今年二十六,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2月19日,父亲头七这天,武汉人黄健在朋友圈发文悼念。
在这之前,86岁的舅舅、53岁的表哥也走了。
黄健的舅舅一直未能确诊新冠肺炎,但出现了咳嗽、发热等症状。一直照顾他的儿子也出现了类似症状,并在老人去世后确诊住院,随后不治。
黄健的父亲并非死于肺炎。过年前,老爷子因中风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住院,随着疫情趋紧,这家医院被纳入第一批公布的新冠定点医院名单,医生开始劝说像黄父这样的住院病人家属,需要在22日前离开医院。
黄健还记得医生的话,“这个病毒传染性很强,最好还是回去。”不久,父亲因呼吸衰竭去世。
“后来给殡仪馆打电话,车子5分钟就到了,车里已经摆了6具。”黄健说,没有告别,没有仪式,家属被告知,疫情过去之后,他们才能去殡仪馆领骨灰。
黄健说,随后一周,他陷入沉默,无法集中注意力,只是一直翻手机,看些无聊的内容。回想起来,他甚至庆幸父亲走得及时,因为再晚两天,他连自家小区都无法出入。
在父亲去世后的40多天里,黄健平均两天一斤白酒,这是他居家期间唯一的消遣方式——麻醉自己,逃离现实。

武汉封城。本文图片 新华社
困城之痛
1月23日10时,武汉“封城”。物理上,这座千万人口城市与外界联系中断,但情绪仍相连。
2月20日,谭咏梅接到了来自武汉的第一通电话。
来电者是一位本要离汉回老家的男子,因为封城,孩子和父母一家四口人陷入困境。电话中她得知,倾诉者的父母和孩子都生了小病,男子非常自责,他每天盼望疫情结束,没想到事情发展远超想象,自己非常疲惫。
初步评估下来,倾诉者陷入焦虑和无助的情绪中。谭咏梅告诉对方,先做深呼吸,让自己放松。
她非常理解这名男子的感受,她告诉他,没能让家人过个好年不是他的责任;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家目前都很平安,没有人被感染,还团结在一起,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是最早提供心理援助的平台之一。这里面向全国求助者,提供电话、语音和文字三种心理咨询。
谭咏梅本是桂林理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负责人,疫情后到平台做了志愿者。她评价自己,作为心理咨询师有着朴素的热情,对他人疾苦,总不由自主生发同理心与关爱。
自2月24日开通至3月7日,热线平台共配置咨询师1798人、呼入总数6319人次、接待总数3862人次、危机总数54例。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宗奎是上述心理咨询平台的发起人。
在他看来,与封城之初相比,老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已基本建立,担忧有所缓解,韧劲也被激发了出来。
但是,“持续这么久,市民的心态和需求都要有舒缓。”周宗奎认为,在宏观布局之外,深入社区,进入家庭内部,激发内生能量,是将情绪消释的关键。
具体来看,政府要突破“最后一公里”,把软性的资源传递到家庭中去。比如一些活动游戏的示范,激发家庭成员互动的建议,或是心理援助热线。“在事情完全过去之后,一定时间内,可能很多人也需要心理能量来修复自己的情绪。”
彭婧是武汉市武昌区水岸新城社区书记,她觉得居民情绪已有了很大改善。
情绪的顶点在刚刚封城之初。从1月31日起,每天社区工作人员都会将疫情公告发到业主群中,眼见小区确诊病例升至25,有些居民当时面临没有床位,情绪比较激动,“说实话也只能尽力去安抚,我们的解释其实也显得很苍白,是的,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
在业主群,彭婧和同事还会发一些近期利好消息,比如疫苗研究进展等,给所有人积极导向。对于个别家庭尤其是病人家庭,社区工作人员还会一对一沟通。

心理疏导工作者通过电话与留观人员交流。
灾后漫长的阴影
至暗时刻已过,但心理治疗持久战才刚开始。
汶川地震发生半年后,中科院心理所在绵阳地区对不同中小学的6000余名学生调查显示,灾后半年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达12.7%-22.1%,明显抑郁症状者达13.2%-21.5%,明显焦虑症状者达20.2%-29.9%。
灾后一年调查,PTSD筛查阳性人群还高达13.4%,焦虑人群达22.7%,抑郁人群达16.1%。
此次让谭咏梅印象最深的求助者,正是一名曾经历汶川大地震的男士。当年灾难中他身体受伤,在随后的十年里生活一直不易。疫情好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他累积多年的悲伤。如不是因为家庭和爱的人,他甚至会选择轻生。
谭咏梅记得,接这通电话时,自己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她非常佩服倾诉者的坚强和毅力。
她不断与对方沟通,帮助这名男士找到走下去的资源、支撑他前行的力量。事实上,这位求助者已表现出了较严重的抑郁情绪,谭咏梅建议他与精神科医生进一步沟通。
往往在与求助者沟通后,因为情绪的共卷,咨询师自身也会受到影响,有时会觉得力不从心。谭咏梅有10多年心理咨询工作经验,她明白,不能让来访者的情绪过度地引导自己。“我们家有二宝,跟家人互动,感受下温暖,调整好情绪再去面对下一个来访者。”

心理疏导工作者发微信鼓励留观人员。
呼唤体系
咨询师可以靠片刻温暖“回血”,但漫长的灾后心理重建,需要强力体系去支撑。
中国第一例有据可查的心理危机干预在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事件后,部分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随即派出一支专家队伍,前往灾区实施了两个月心理干预。
随后1998年长江流域洪灾、张北地震、2000年洛阳火灾、2002年大连“5•7”空难都有心理干预者参与其中。
但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干预,我国仍缺乏细致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孙煜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提到了心理援助,但对心理援助的主体、流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
孙煜华觉得,面对巨大的疫情压力,当地政府已力有不逮,如法律没有明晰责任认定,心理干预可能变成“走过场”。
他建议,立法部门对《精神卫生法》第十四条进行专门解释,同时明确建立心理干预专家库、财政和政策保障制度,特别要针对重创伤者的心理恢复,建立一套长效的干预机制。
或者由民政部、卫健委、应急管理部等部门针对公共突发事件联合出台规章,将心理干预的具体流程和主体、责任讲清楚。
而当前,法律尚未齐备,孙煜华认为政府应该先发文件,把心理干预操作指南做成小册子,发给社区工作者。
他特别强调,政府特别是社区层面,应该摸排居民,对心理问题较严重居民进行提前干预,“在长期居家过程中,心理‘燃点’可能会降低,”孙煜华指出,政府应该把心理干预放在更高层面上看,保证社会稳定运行。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蓉则呼吁,灾后心理干预工作,非政府组织不可或缺。
据统计,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半年后,志愿者由2万人降到1000多人,剩下的几乎都从事心理干预的工作。在美国,其红十字会设立了灾难心理服务人力资源系统,用以招募志愿者,以备不时之需。
在专业技术、组织机制上,由于灵活、自发等特点,非政府组织有着政府无法比拟的优势。曹蓉认为,建立起应急管理心理干预的长效机制,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携手——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健全心理干预体系、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发挥作用,而非政府组织提供心理干预的人力资源、技术保障以及科学研究。
市井喧哗将回归
不过无论如何,对比汶川地震,如今的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干预在组织上和理念上,都有了长足进步。
如今在雷神山医院任心理工作组组长的程文红,曾经历过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7日,灾后第5天,她就随队前往绵阳灾区,当时,各种医疗队、心理咨询志愿者一哄而上。
“有点英雄主义。”她说,医生习惯了诊室里接待患者,来到灾难现场,常规诊疗模式不适用了,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危机干预。
这次在武汉她看到,地方会统一各方需求,国家卫健委统一调配资源,何时介入?需要多少医生?物资缺哪些?……效率提高了很多。
而对于心理干预,大家普遍能理解了,尽管这次很多人是第一次经历重大灾难,“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是理解这件事情了,只不过就是经验多少而已。”
借酒消愁的武汉人黄健似乎正迈出阴影,虽然不知靠的是时间还是酒精。
明显的标志是,他开始重新在亲人群中抢红包,尽管3月8号的红包不是为他准备的。慢慢地,他也开始关心身边事:从不下厨的他也开始研究菜谱,“鲢鱼怎么做不腥?”他开始抱怨烟不够抽了,爱抽的品牌现在每条得加价20元……身边的亲人能感觉到,那个节俭精明的他又回来了。
4月8日,武汉市将解除离汉离鄂管控措施,这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和900万市民一道,在“暂停”2个多月后,逐步恢复正轨。看惯了江水的潮起潮落,在短暂的沉寂之后,标志性的市井喧哗将重新萦绕武汉三镇。
这段属于他们的群体记忆,会在个体心中留下各自印记:深浅不一,大小各异……有些人能够通过时间去抚平创伤,也有人需要“拉一把”。灾难之后,克服恐惧,才能真正重归生活。
原标题:在武汉“治心”|危机之后,心理干预如何避免“走过场”?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