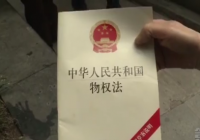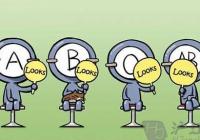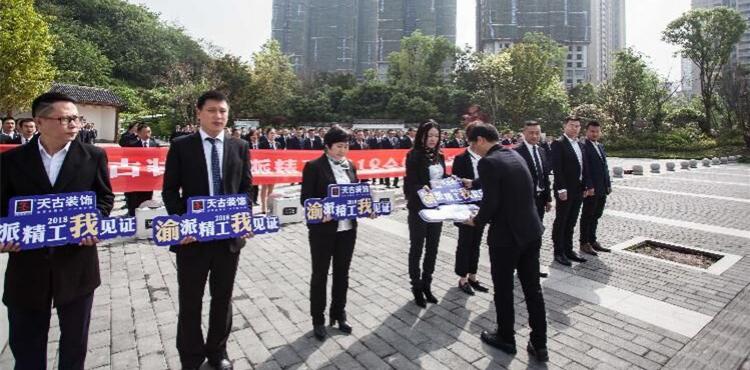本文原载于《南方日报》2008年04月07日
30年前,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一经小平亲手开启,在南中国,一批改革闯将“大闹天宫”,“杀出血路”,不仅让中国从此跟上并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更成为我们30年来时时重温理想、重获力量、重执方向的丰沃资源。
今天,站在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荡胸生层云,欲以解放思想的话语体系,以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的宏阔叙事,续写改革开放新篇。此时,改革闯将的智慧与勇气,更闪耀着夺目的光茫。我们怎样开垦这一丰沃资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能开拓出一个怎样的现在和未来。
吴南生,就是当年的重要闯将之一。让我们走近吴老,且听他们如何“大闹天宫”,“杀出血路”。
广东经济特区的酝酿
卢荻(以下简称卢):吴老,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首期,你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还兼任过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领导者和见证人。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为了回顾历史,现在请你谈谈当年创办广东经济特区的有关情况。
吴南生(以下简称吴):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十年浩劫”之后,百废待举。在这历史转折关头,1979年1月8日至25日,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我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汕头是我的故乡,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1936年,我在这里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由党组织安排,赴延安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后,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我们凭两条腿从延安奔赴东北。1949年随解放大军南下,参加解放汕头市,担任市军管会副主任。1952年,我奉命调动,离开了汕头地区。
这时,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呈现在我眼前的情景,简直令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一派贫穷落后的景象,不禁为之心寒:那些我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这些人一些是在那“备战、备荒”岁月随工厂迁到大小三线去的汕头人,一些是一次又一次上山下乡到海南、粤西的知识青年。而今他们又返回家乡汕头,由于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只好栖自住在大街小巷临时搭建的竹棚里,人们故意把这些竹棚戏称为“海南新村”。汕头过去有限的骨干工厂,已迁到三线去,经济很不景气。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眼前情景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汕头曾经是中国南部一个对外开放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早在五口通商时就开始了。恩格斯也知道汕头这个地方,他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其它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解放初期汕头还是一个商业很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高楼大厦林立,经济一片繁华。而眼前的汕头市,却如此贫穷落后,满目凄凉。重返故园,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痛地说,眼前的汕头,“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
卢:你这次返回故乡,眼前景象对你无疑是很大的刺激,你是否已感觉到非改革不可了?
吴:是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次我在汕头呆了两个多月,先后参加了汕头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各县市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对汕头当时落后的状况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段日子我晚上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出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一幅江山啊!解放都30年了,人民群众生活还如此艰难,我感到十分内疚和困惑,特别有愧于那些当年舍生忘死、鼎力支持革命的父老乡亲。
我内心非常焦虑,感到我国搞了那么多年穷社会主义,将国家搞到这么穷,这么绝对化,觉得非改革开放不可。这几年,我较多地见到叶剑英元帅,他多次焦虑地对我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
这不仅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和期望,也是国内老百姓和海外爱国同胞、港澳同胞的呼声与愿望。用什么办法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呢?我征求过许多老同志和各界人士的意见,也和从海外、从港澳回来的朋友交谈,寻找改革开放的方案。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在50年代,我曾分管过香港的部分工作,在海外有许多爱国的朋友,经常往来。我对港台等海外经济信息了解比较多。这一提醒,我的脑际立即如电光火石般闪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急着征求汕头地委领导的意见,征求乡亲们的意见,大家都举双手赞成。
2月21日深夜,我正感冒发烧,但心情激动,迫不及待地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电报在指出汕头存在的突出问题后写道:“来后,我还同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研究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和扩大对外贸易的问题。汕头市解放前是我国重要港口之一,货物吞吐量最高年份达400万吨,海上的客运达35万人。汕头地区劳动力多,生产潜力很大,对外贸易、来料加工等条件很好,只要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内外积极因素,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让我们放手大干,这个地区生产形势、生活各困难、各方面工作长期被动的局面,三五年内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已拟定了一个初步意见,待报省委研究。”我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以扭转汕头地区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
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到广州。晚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就到我家中,两人交谈了很久。3月3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先走一步那个“子”怎么走呢?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华侨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外面很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我义无返顾地说,如果办不成,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当时常委们都表示赞成,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他说,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1、2日,在杨尚昆同志的主持下,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但对深圳、珠海和汕头“先走一步”的三个地方怎样“正名”,一时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些,在当时可是天大的罪名啊!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先上报中央。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我前往看望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向他汇报先走一步的设想,叶帅非常高兴,很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中央(1979)50号文件的制定
卢:中共中央(1979)50号文件是如何产生的?
吴:4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开始,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同意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并定名为“出口特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5月14日,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达广东,和省委共同起草一个解决广东“先走一步”问题的文件。在这期间,谷牧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中央有个意见,汕头办特区的条件不够,只办深圳、珠海,你的意见怎样?我说,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并没有办特区,我也不负责办特区了。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故乡,而是办特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开始的,海外和港澳的朋友们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谷牧说,呵,要讲信用!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我说,行。这就是中央决定缓办汕头特区的内情。
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备受粤闽两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迎。
主管广东经济特区工作
卢:请你谈谈“三人小组”的情况。
吴: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和我组成的三人小组,省委还决定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
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于是,我全力负责全省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我原来主管宣传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这时,我请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高等院校的校长、党委书记到省委会议室,尝情地对他们说:我要“弃文从商”去办特区了。多年的经验,经济不发达,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是发展不了的。希望特区能办成,赚了钱,支持你们大力发展文教科技事业。之后,我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一别就30年过去了!要知道,宣、教、科、文战线是“十年浩劫”中受劫难最惨重的,以后,在改革开放中,他们是最积极的支持者。
9月28日至10月5日,我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秦文俊、外经部门王志义等同志到深圳,走访了沙头角、蛇口和几个边防口岸,同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边看边议,在许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我们对解决深圳市今后建设的问题,同市委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当时深圳经济非常困难,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币,同期香港新界农民收入13000多元港币,两地农民收入差距很大。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外逃的共有六七万人,耕地丢荒9万亩。新成立的深圳市委要以很大的精力去抓“外逃风”问题。原来的深圳镇仅有3万人,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深圳改为特区后,市委对重点抓什么,经济如何规划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和市委负责人经过反复交谈,明确了解决“先走一步”这一首要问题,强调要力争在较快时间,在深圳建成一条“富线”。
我们回到广州之后,于10月24日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关于蛇口工业区问题,这时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地租价格没有定下来,影响同外商谈判。招商局认为省里定的价格偏高,对外商缺乏吸引力。我在报告中提议,按招商局的要求,每年每亩上缴广东省4000元港币,从“六通一平”完成后开始征收。11月18日,由我主持,省、深圳市和招商局的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建立蛇口工业区的问题,至此全部解决。蛇口工业区从此成为深圳持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先行和示范的部分。
1979年月10月31日,我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随后,为省委草拟了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出口特共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卢:“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是怎样确定下来的?
吴:同年12月17日,谷牧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中央各部委办的有关方面负责人都参加了。当时,在北京是一次很轰动的会议。会上,我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汇报广东筹备建立特区的情况,我说:我们的意见是,建立特区必须采取“一快二宽”的方针。快,就是既然看首席代表了,就要立即动手,不要拖拖拉拉,犹豫不决。要大胆放手,争取时间,奋斗10年,把深圳、珠海、汕头3个特区建设成为初步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在那里建立一条富线。我还提出,将“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的名称较好,含义更确切。我解释说: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文化等事业。在汇报中,我还提出参考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特区土地使用期定为50年。
广东、福建汇报后,谷牧就特区建设等问题作了讲话。他十分赞成深圳特区的路子。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会议确定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下达。
这年4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5月4日,省委、省政府任命我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副省长王宁、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对全省三个特区的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6月12日,省委任命我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制定
卢:创办经济特区,要做的事很多,为什么要先抓制订特区条例?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起草特区条例的?
吴:中央决定试办特区之后,海外的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我感到当务之急就是要起草拟定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我们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
可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其他人也不懂,国内无法无天几十年了,老人家就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怎么办?还得请海外朋友帮忙。当时主要是通过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等老朋友,收集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出口区的资料。我们对这些收集来的海外许多有关的法规进行了分析研究,适用的就照搬过来,要修改的就修改后再用。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地租”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打倒了地主,怎么又要收地租呢?后来我们就改称“土地使用费”,大家都觉得很好,很社会主义,反对的人也没意见。说“地租”就不行,中国人很重名分的!
研究、起草特区《条例》。这个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了一年的时间,作过13个草案文本。
《广东省经济特区大事记》中记载:1979年7月15日,中央、国务院决定试办出口特区。8月15日,由省委书记吴南生主持,邀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省委党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部分学者起草特区条例;8月21日又邀请港澳经济界及有关人士45人举行座谈。
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条例。以后,国务院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论证。
1980年4月14日,我向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了《关于我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这时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正好在广东视察。我请他把条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叶帅非常支持。
同年8月26日,叶帅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条例》的说明。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我们还起草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治安保护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公布,意味着中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也使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难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完全消失了。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和高兴。
“罗湖风波”
卢:在创办经济特区过程中,爆发了“罗湖风波”,具体经过是怎么样的?
吴:我兼任经济特区工作后,即着手组织制订特区的总体规划。在谷牧同志的大力支持下,1980年5月,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和工程师108位,组成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和航测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分组、分片、分段设计和多种方案的比较,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
建设深圳特区的方案,经过多次的讨论、比较。最后确定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大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约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
原先打算开发上步或福田区的土地,但一场大雨促使我们改变了初衷。
1980年7月27日,一场大暴雨把罗湖一带淹成一片汪洋泽国,我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住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喊救声。我卷起裤腿,趟着没漆的大水,找到了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急切地要求他一定得把水治住,否则难以建设特区。刚考察灾情回来的罗昌仁,与我深有同感。这时,我们和工程师们都住在一起,不断探讨有关规划大大小小的问题。工程师们粗略估算一下,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以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巨额资金。这时,邓小平同志已在全国多个地方说过: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为钱而发愁,兴感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于是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谷牧当即慨然答应可以帮助要点贷款,并询问用途及还贷办法。
我解释道,深圳特区原来有先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回一场大小使我们更认识到,工程师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可以改变国门的面貌,解决年年危害的水灾;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的投资。接着,我介绍: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每平方米90元搞“五通一平”,要7000万元。开发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左右,总计可以收入20亿港元左右。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我提出的这一做法切实可行,答应先帮助贷款3000万元。我喜出望外,对谷牧说,有了“酵母”,特区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旁白:据作家查阅深圳市委、广东省委有关这一问题的会议纪录和有关资料,“罗湖风波”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10月初,用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大家都为有了贷款而高兴。可是当讨论到先开发罗湖小区时,却爆发了轩然大波——“罗湖风波”。工程师提出,罗湖毗邻香港,是一片旺财、旺地,黄金地段,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特区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但没想到有的领导居然站出来反对。他们提出,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不如将这些钱用来搞农田基本建设。
双方唇枪舌剑,各摆各的道理。工程师们认为某些市委领导不懂得城市建设,更接受不了那种高高在上、动辄训人的口气。于是,有一位年青气盛的工程师和两位年长的常委拍抬打凳,互相对骂起来。会议顿时陷入了僵局。
当时吴南生主持会议,冷静而详细地听取双方的争论,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他才旗帜鲜明的支持工程师们的意见。并当断即断,一锤定音,决定立即动工,搬掉罗湖山,填平低洼地。他说:如果现在不坚决作出决策,耽搁了组织队伍和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的时间,很快,雨季就要到来,移罗湖山填高罗湖洼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个特区建设也同样要拖延多一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做!
不久,挖土机、推土机出动了。富有城市建设经验的罗昌仁和舒成友,一面组织千军万马,开始移山填洼,搞“五通一平”,罗湖呈现了一派愚山移山的气势;一面集中力量治水;从梧桐山到深圳河,在地下用钢筋水泥修筑一条可以并行两部大卡车的大排洪沟。
市委内部有的人不知出自什么动机,竟然乘任仲夷才到广东,吴南生回省开会的时候,不经过市委任何成员,私用市委名义发电报给省委,状告开发罗湖是瞎指挥。有人还公开出面横加干预,挑起争论,并多次下令停工。
任仲夷看到电报,立即亲自到深圳,从多方面作了调查,听了不同意见。在当晚的市委常委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建设中要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你们意见不一致,为什么不很好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呢?”“搬罗湖山,是特区第一个大工程,你们今后要做的大事还很多,要讲团结。”
12月8日至10日,谷牧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江泽民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12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江泽民在会上提出:“深圳特区的建设要引起足够的重视。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在谷牧、江泽民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委对建设深圳特区,首先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达成共识。那些曾一度极力反对这一意见的人,最后也只好悻悻然地接受了现实。至此,“罗湖风波”从平息下来了。
在成千上万建设大军的日夜奋战下,80多万立方米的罗湖山终于夷为平地,罗湖小区陡然填高了两米,低洼处填高了四米。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
不花国家的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城市(这是计划经济绝对办不到的),深圳经济特区的这一实践,是它对全国的又一个贡献。搬掉罗湖山,建成罗湖小区,是深圳特区的决定性战役,没有这一着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经济特区的最大贡献是引进了市场经济
卢: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今天回顾创办经济特区坎坷曲折的历史,特别是回顾当年受到各种非议,争论特区会不会成为“租界”和“殖民地”的时候,你一定感触很深。
吴:当年我们受到的压力确实很大。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到1982年初,寒流滚滚南下,明枪暗箭,纷至沓来,对广东——尤其对经济特区的压力,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谷牧后来回顾说,全国各地的非议之词,“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我是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这代表了我从事特区工作的同志的心情。
五年后,即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说:“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抗日战争用了八年的时间,创办经济特区到这时也是八年的时间。过去了的时间就是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要经过时间的,时间记录了实践。有关当年的种种事故,就不必再提了吧。
卢:你认为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吴: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当时别人明白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我心里很明白,办特区,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自以为是的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新路。我们在1980年底即特区条例经全国人大批准公布后,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面对各种非议,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过“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要知道,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辞,罪大恶极啊!可谁能想到,20年后,我们中国却要求人家要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卢:是呵,当时那么多“左”的思想,人民群众中也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你们当时的勇气是从何而来的?
吴:小平同志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从创办特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从事这项巨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际工作方面要有勇气,在理论思想上也要有勇气。没有两方面的勇气是“闯”不成的。
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前面说过,1979年8月15日,我已邀请广东的多位学者一块研究特区条例,同时座谈、研究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要闯过这一关,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省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中,曾非常明确地讲出我们的观点(即广东理论界的观点)。
这是我们28年前的论点:
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时继承它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事实上,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俄国,却不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特别强调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有用的管理经验。列宁讲过:“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文稿》第3卷)
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列宁的思想前后有什么变化,也是因为有了理论勇气,对那些吵吵嚷嚷,“不去跟他们一般见识!”好!你“正确”,你表演吧!我就不开口,你要吵就自己吵吧!我“只做不说”。你能怎么样?
但是,这些都已经是28年前的事了!
卢:改革开放就30年了,一定会有许多体会吧?
吴:体会?谈不上。不过,也常常会回顾过去的岁月,思考一些问题,有时,也有一点想法。例如: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都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什么叫文明?这就是文明。
关于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必须不断规范的问题,但这已是属于实践中的问题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分析和确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历史任务,要下点苦功夫,不是给它戴上一项“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能解决得了的。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证法》)这句话很需要时时谨记,认真实践。
我在1981年后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但省委分工我继续分管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工作,经常在三个特区间奔走,是省委领导集体中有关特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后,我从省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时止。
真的,没有想到,怎么一下子就30年了呢!
原标题:吴南生回忆改革开放艰难起步: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