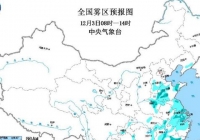1949年11月30日,重庆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图为部队进入解放碑。
重庆党史微信公众号消息,1949年11月30日,对于其他人来说,那只是平常的一天;可对于我们重庆,那是一份厚重的历史,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今天,我们与重庆解放的亲历者一起去感受当时人们迎接解放的兴奋和喜悦。
先遣部队有惊无险“杀进城”
讲述人:杨国宇,时任二野三兵团十一军参谋长
刘伯承、邓小平命令:二野三兵团速歼长江南岸之敌,相机占领重庆。
二野三兵团决定:十一军、十二军从正面分路挺进,乘重庆外围仅有胡宗南第一军布防,迅速夺取之。
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兵临南岸。敌军望风披靡,逃往成都。战局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十二军折道直奔成都。十一军军长曾绍山急令:“只有穷追,才是胜利。”军参谋长杨国宇及三十一师副师长兼参谋长胡鹏飞率先行团,渡江登岸,解放重庆。
这是1949年11月下旬的事情。
11月29日下午3时左右,我和胡鹏飞带陶怀德先行团抵达长江南岸的南温泉时,在李家沱鱼洞溪歼敌一个营,俘敌200余人(在这次战斗中我师长赵兰田同志负伤)。据俘称:他们是胡宗南一师一团一营,由汉中乘汽车昨晚才赶到此地,任务是迟滞解放军西进。我们问:“重庆情况怎样?”他们说:“我们刚过河来守南温泉,听说你们要来,大部队连午饭都没吃就过河去了,我们正准备走,你们就来了,那边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看来,他们说的是实话。重庆就在对岸边,可是看不见。
15时左右,李家沱对岸九龙坡杨家坪燃起了熊熊烈火,浓厚的烟雾几乎笼罩了半边天。不到半小时,整个北岸就变成了“火城”。汽油桶“轰轰”的爆炸声,木板船“啪啪”的燃裂声和对岸敌人打过来的炮弹声、机枪声不绝于耳。许多战士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跑来情战:
“快下命令打过去吧!晚了,重庆就会变成彭水呀!”
我的心情也十分焦急。彭水被敌人放火烧毁了,难道还要重庆重蹈其辙么?绝不允许!我们必须把重庆这座闻名于世的山城完完整整地交给人民。我稍加思索,转身对陶怀德团长说:
“我们只有3只小船,是命根子呀!我和胡鹏飞在这里打手电筒作信号,叫部队打枪打炮佯攻,如敌人不还击,你带上一个排强渡。要记住,时间决定着重庆的命运!”
3只小船摇成“品”字形,向对岸急驶。我从望远镜中看见对岸混混浊浊,船靠岸后,战士们象猛虎下山,扑进九龙坡,但很怪,没有遇到敌人的阻击。不一会儿,才传来象似机枪扫射和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我的心一沉,莫非中了敌人的埋伏?
突然,我身旁的战士们欢呼转跳起来。抬眼望去,但见10余只木船向这边驶来,船夫们高声吆喝着:“不要打抢!我们是帮解放军渡江的!”
我和胡鹏飞分别乘船来到北岸,没见到陶团长他们,就问一位老头:“刚才枪声在哪里响?”
老头嘿嘿一笑,用手掠掠胡须,说:“哪里是打枪,老百姓们放鞭炮欢迎你们哩!那些国民党兵没敢放一枪,全跑啦!”
我带着登陆部队向浮图关急奔。半路,赶上了陶团长。我向他作了简短的交代:
“敌人一定有破坏重庆的计划。我们必须在晚上七点半以前进入城内。你还是打先锋。”
陶团长问:“路上遇到小股敌人怎么办?”
我说:“别管它小股大股,都统统甩掉,留给后续部队来解决,你只管往重庆城里钻。”
陶团长笑了:“我明白了——哪怕只先进去一个兵,也会给留在重庆的敌人、特务以巨大的精神打击。”
浓雾蒙蒙遮住了重庆,我们无法看清山城的真面目。但见白市驿方向一片火光和轰轰的爆炸声,团团烟雾腾入高空,隙间不时显出细高的工厂烟囱,正北及东北方向,也传来了天崩地裂的爆炸声,间或有建筑物倒塌的巨响。残暴的敌人已经开始下手破坏了。战士们愤怒得咬牙切齿,一股劲就冲到了全城的制高点——浮图关上。
在浮图关,有被陶团长甩下的敌国防部警卫第二团。这个团的一千六百多名官兵自知大势已去,不愿再为蒋介石卖命,所以,胡鹏飞没费多大劲儿就和平地解决了他们。
浮图关下就是新市场的大街。街面上有许多地方用桌椅围成了圈圈,中间竖着长凳,上面写着——“注意地雷!”市民们传过来招呼:“那是我们标的,里面有国民党埋的地雷,不要进去呀!”
我和胡鹏飞决定,后续部队不从浮图关入城,绕山路走捷径,直插化龙桥、小龙坎,与先锋部队构成钳形攻势,以防不测。
天已经黑了,又下起了蒙蒙细雨。
我们沿着山上很陡的石阶小路一步不停地跑,心“砰砰”地狂跳,好象要蹦出来。没人喊苦叫累掉队,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截断残敌向山洞的退路,保住城市不受破坏!
11月30日凌晨4时,部队抵达化龙桥、小龙坎。张营长从前面赶回来,说:“前头的敌人真多,还有不少散兵游勇队伍。他们也搞不清我们有多少人马,吓得要死,一接火就投降。”胡鹏飞用手电筒往街上照,看见了一排排的俘虏兵。
张营长又说:“还有地方上的汽车修理厂、化学厂、玻璃厂、卫生器材制造厂和电信器材制造总厂,都派人和我们接头!”
我让人找来几位工厂的厂长,对他们说:“从今天起,工厂是人民的财产了!你们保护了工厂没有让国民党破坏,也有一功!”
电信器材制造总厂的厂长说:“你们还要向前走吧?这一带工厂多,护厂总得有个挑头的呀!”。
我说:“数你的厂最大,你就做做这个工作吧!”
他说:“你得给我个执照。”
我在一张小纸片儿上写下了这个意思,又签上了我和胡鹏飞的名字,让他拿去联络各个工厂,并以此与后续大部队接通关系。由于战事紧张,我们未及时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解放军进城的消息惊醒了化龙桥,市民们高兴地放起鞭炮,汽车修理厂的工人把所有能启动的汽车开来送给部队使用,这其中还有几辆吉普车,上面张贴和挂满了标语、鲜花。在一片欢呼声中,战士们上了汽车,许多老百姓动手帮助我们搬运油盐担、重机枪、小炮和炮弹箱。这些都是我们的指战员用肩头扛到重庆的。
汽车队驶出化龙桥,很快就推进到新桥。歌乐山的敌人刚刚逃去,没来得及把桥彻底毁掉。我们找来木板铺上,就顺利地通过了新桥。
在一座公路山洞前,我们被一堆堆敌军的尸体和毁掉的汽车挡住了去路。我很纳闷:我们是先头部队,脚下又有飞快的汽车轮子,前面不会有十二军的其他部队,而友军再快不过才到白市驿,这股敌人是谁消灭的呢?后来才知道,因为我军推进神速,都说是杨森刚刚逃过山洞,就不管后面自己的汽车十六团和陆军大学的官兵,下令爆破,企图迟滞我军。
我门把敌人的尸体掀在一边,清理了公路上堆的飞机炸弹,就顺坡而上,通过山洞,经过歌乐山,直逼中和场。这时,友军已占领了璧山,我们又顺手抓住了一股逃窜的敌军……
我们保住了重庆,山城获得了新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重庆市郊入城
兵不血刃解决长江舰队
讲述人:李钦哲,时任四野141师423团政委
11月30日下午4点多钟,重庆已历历在望。为了保证商船的安全,轮船在江北区以北的青草坝停靠,并请了几位船员作向导。团侦察股长滕锡高带侦排先下船,去嘉陵江边摸清情况,各营分路向嘉陵江边开进。下船后弄清了江北区已没有敌人,只有少数保安队。为了打好解决长江舰队这一仗,除一营外,又抽调了三营机炮连和九连参加。
到了嘉陵江边,除了侦察排和各营派少数人去找船外。部队一律在街内隐蔽休息。据说朝天门码头没有敌人,而市内情况还弄不清楚,重要的是敌人兵舰还在,人没有跑。作向导的商船船员办了件好事,找来了江北水上派出所的人,他们对兵舰非常熟悉。指出靠近朝天门码头那只是敌旗舰“民权”号,其它4艘舰都停靠在长江东南岸的深水线中。各舰之间有一定距离,停靠的面比较宽。团和一营研究先集中精力打这突出的敌旗舰,解决了它,其它的舰就好办了。决定先由侦察排和一个连前去,看情况的发展,后边几个连再行动,部队需要的木船,都停在朝天门码头附近。为防止敌舰东逃,三营机炮连在嘉陵江口北侧占领了阵地。
下午6时许,天已黄昏,敌旗舰上的灯已发亮,侦察排和一连同志们持着枪,拿着手榴弹向敌旗舰驶去。在离敌舰二、三十米时,敌人还没有开枪,于是侦察排和一连就向敌人喊话:“我们是解放军,放下武器,不要抵坑,我们宽待你们!”敌人不但没有反抗,反而拉起了汽笛。我们在朝天门码头水上派出所的小艇上,问是怎么回事,派出所的人说:“好了,好了,他们鸣汽笛是表示欢迎你们。”接着,派出所的小艇也鸣起了汽笛,由近及远,所有江上的机动船都自动地鸣起了汽笛。响声划破了夜空,又加上山城的回声,江面上一片轰鸣,十分雄壮。
由于兵舰已解决,团立即派一营和二营一起向市内搜索前进。旗舰只由侦察排上去,并留下九连归侦察股滕股长指挥,接收整个舰队。滕股长带侦察排上舰后,解除了哨兵的武装,进了座舱。少将舰队司令叶裕和站着拘谨地说:“欢迎,欢迎!国民党已经彻底完了!给我们的命令是死守重庆,而他们昨天晚上却悄悄的撤退了。今天早上才来人要我们把船凿沉,上岸撤往成都。我们没汽车,怎么走?所以,我们不愿再犯什么罪过,等你们来,把舰交给你们。”
他这话说明了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是非常仓促的,蒋介石当时坐镇重庆,想死保重庆不放,在山穷水尽时不得不仓皇撤退,他本人是30日拂晓才从白市驿机场,无可奈何地飞向成都的。接着,滕股长问他:“其它几只舰怎样?”他说:“各舰都同意,请诸位去接收。”他马上让信号员向各舰发信号,信号发出后,4只舰都作了同意的回答,并且都开亮了全舰的灯,江面上一片通明,全舰队一目了然。经过商定,滕股长让九连乘舰上的小艇分赴各舰,封存了武器,冻结了公用资财(该舰队有20多箱银元),并对官兵分别进行了教育,舰队就这样被解决了。

重庆市民向二野司令员刘伯承献花
“天亮了”“饭碗”保住了
讲述人:满爷,时廿一兵工厂任驻厂检验员
1949年11月29日早上。
我跟平时一样,准时去上班。
当时,我在廿一兵工厂任驻厂检验员,我们的办公地点就在厂部旁边一栋叫“勤园”的小楼二楼。
我去上班的目的就是想探探消息。
几天前,我到兵工署(现枇杷山公园旧址)领遣散费时,看到署里从南京逃来的一些熟人都不见了,办公室显得冷冷清清。
转了一会,碰上同班同学李宗鲁。
他见到我就说:你怎么来了?我们已经听到炮声了,一些头头都已经开溜了。
言语之间非常警惕,示意我赶紧离开。
我说:不是要我们今天以前来领遣散费吗?
他很快把我带到门口一间办公室,好在发放的人还在,经他介绍之后,我领了一两黄金和两个银元,还给远在昆明的同班同学黎拒非代领了一份。
这些硬通货对我来说求之不得,战乱时代,可以在困难的时候应付一下。
回家以后,我妻子很快就把黄金缝在每人的一只鞋跟里,银元即随身带着,做了最坏的准备。
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有几大杀戒,“造谣惑众”“扰乱社会秩序”都在杀戒之内,所以我从署里回来之后,仍然装得跟往常一样,只在熟人之间相互传递点消息。
当我把在兵工署听到的、见到的告诉步枪所副所长谭蜀才的时候,他却把手掌往脖子上一抹,彼此心照不宣,我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今天情况不一样了。
当我走到厂部办公室附近时,见到厂门口涌进不少军人,厂部大门口站岗的也全换了。
我走进办公室,一位帮我们做勤杂工作的工人师傅告诉我:这些人进厂了,要清办公室,你赶紧离开。
我很快清理了一些必须带走的东西,就往回走。
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一队军人正往厂里一箱一箱的搬炸药,我们村子附近的工具车间也有人正往里搬。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好,他们要炸毁兵工厂,我们村子也会遭殃!
我飞奔着赶回到家里,妻子正急得团团转,一见到我,就把一个大背包递过来,她身上也背了一个背包,回身锁上门就走。
我们决定去离厂区较远的宁和村、同班同学陈宪文家里暂避。他家里只有三间房,有母亲、一个哥哥和三个妹妹,本身就够挤了,加上我们夫妻和后来的同班同学李廷辉,就显得更挤了。
但他们一家人都很好客,伯母更是把我们当儿女一样看待。我妻子当时20岁,和她幺姑娘同岁。我妻子平时也一直“幺娘幺娘”地叫得很亲切。
李廷辉更是一个好热闹的人,虽然是避难,大家却相处得融洽而欢乐,而且也知道这避难时间不长,因为当时的“国军”只有跑的份了。
当晚,我们既担心散兵游勇的胡作非为,更担心整个兵工厂会被炸毁。一整晚谁都睡不着觉,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深夜,我们先后听到两声巨响,一远一近。听起来好象是厂区和嘉陵江边。一些胆大的还跑到室外去看。
但谁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村子旁边的一条马路成了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它是通往外面大马路的唯一通道。
我们都尖着耳朵细听着动静,但后来没有听见大的声响。过了好一阵,心情慢慢的平静了,估计国民党军队可能已全部撤离,不会发生战争了。
紧绷着的神经完全放松,坐着坐着我们就开始打盹了。大家睡意正浓的时候,忽然间有人高喊:解放军来了,正在马路上休息咧!
此话一传开,大家睡意全消,纷纷起来去看解放军长得啥模样。
天慢慢亮了,我们也跟着去看解放军。
当时,解放军人数不多,几乎都被厂里的职工包围了,相互之间谈得很开心,无拘无束。这场景大大出人意料,跟国民党的军民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谈话中,知道他们是来护厂的,先头部队早几个小时就过河了。因为他们来得快,国民党的炸厂部队也走得快,炸响两声之后,就再也没有声响了。除了发电厂和刘家台后山储有两百多吨炸药的洞库被炸之外,其他车间都完好无损,几千职工的“饭碗”保住了!
真是谢天谢地啊!
据说洞库被炸的时候,刚好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从刘家台山坡下路过,半边山被劈了下来,死伤了很多人,真是祸从天降啊!
解放军进厂了,我们也亲眼看到了,一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原来设想的许多惊险场面,都没有出现,心情感到特别舒畅。
陈宪文的妹妹还奋笔写了三个大字“天亮了”,贴在大门口,大伙一片欢呼!
原标题:重庆解放69周年|那一天那一夜,我亲身经历解放重庆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